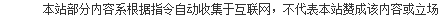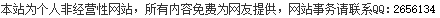有没有一开始就是个错不在自己城镇中心围城墙的打法?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1-04-21 00:55
时间:2011-04-21 00:55
新围城时代 被大城市驱逐的年轻人
普通人对梦想更为实际,挣钱糊口,一个容身之所,一本户口。和这一梦想呈递进关系出现一样,大城市生活的成本和艰辛也在不断变大,大得甚至阻碍了普通人模糊可见的上升空间。
允许人们称为他们想成为的而又不停止他们所是的,允许人们使他们所是的而又不停止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伊塔诺·卡尔维诺关于寻找和失去,这里面一定有一个我们无法解决的原因。当我们怀着不同的梦想来到大城市,在大城市里体会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而我们却发现,在时代进步的背后,是城市隐形的围墙越来越高,越来越厚,以至于挡住了我们突围的方向。突围,有时候仅仅是为了获得这个城市的身份,可是突围,突得我们头破血流。在城市的“高墙”内外,究竟,我们将被什么带领?有两类人通常愿意在大城市逐梦,一种是成熟的企业家,他们有资金,有关系,城市是他们捞金的去处;另一种是普通人。普通人对梦想更为实际,挣钱糊口,一个容身之所,一本户口。和这一梦想呈递进关系出现一样,大城市的成本和艰辛也在不断变大,大得甚至阻碍了普通人模糊可见的上升空间。我们试图关注在大城市里逐梦的各个阶层,观察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在不同层次遇到的不同阻力,这种阻力,正是现在城市给外地人筑造的无形高墙。成为北京人的成本在784万北京“北漂者”看来,熊彦无疑是成功者之一。他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家外贸企业有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并且一度在通州拥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套还是近200平米的复式单元,但他最近却卖掉了这两套房子,与妻子一起带着刚出生的孩子搬到了西二环外月坛附近租下来的一套老房子里。孩子在去年年底的出生让熊彦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在北京拼斗了十几年之后,他仍然没有北京户口。“孩子长大以后,至少要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个北京人,能在北京孩子的圈子里长大,见识也会比回老家宽一些。”熊彦说。北京市统计局最近发布的2012年各区县主要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及在京居住6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达2069.3万人,其中1297.5万人有北京户口;暂住人口为784.2万人,比2011年减少41.6万人,单单是海淀和朝阳两区,没有户籍的暂住人口就已经减少了42万和30万。年轻人正在离开繁荣的中心城区,或者搬到郊区的“睡城”中去,或者离开这让人煎熬的都市,回到自己的家乡。但熊彦却反其道而行之。通州的房子“我现在也有些后悔,如果当初选择留在北汽福田,现在户口早就有了,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奔波了。”2000年,刚毕业的熊彦来到了北京,被北汽福田录用,工作是调度员,但实习期长达一年,工资只有800元。“当时留在福田的哥们都已经拿到户口了,他们是国企,有人事指标,没办法,我这人是走一步看一步,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么多,只是想这800块钱,根本不够我生活的。”熊彦回忆,在第二年的4月,他辞职了,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找了很多工作,干过医疗销售,也干过翻译,由于收入拮据,只好还在福田的宿舍里蹭着住了很长的时间。“后来实在不行了,只能跟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到福田外面租了一间平房,只有7平方米左右,只够放一张床。”熊彦现在还是觉得,当年在北汽福田的日子跟在大学里没什么两样,也就是单位、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福田的地址在昌平的沙河镇,尽管现在已经有了不少的新楼盘,但仍有村房可以外租,不少年轻人选择这里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窝。熊彦在沙河的平房住了一个月,那是他在京最困难的一段日子,他还没找到工作,而当时他也没有什么积蓄。“没有办法,只能拼了命地去找工作了,当时也没想过回丹东去,灰溜溜地跑回去是很丢父母的脸的事情。”熊彦说。一个月以后,熊彦在一家外贸公司找到了工作,并且一直干到了现在。由于赶上了入世后的经济大潮,此后熊彦的日子变得宽裕起来了,而且因为单位提供宿舍,也不用为住处发愁。2005年,熊彦在通州买了一套两居的房子,100平米左右,终于有了自己的房产。当时八通线开通没有多久,通州的房地产开发也才刚刚起步,他总共才花了40万。此后没多久,通州新城的概念开始提出来,2005 年的北京市总体规划中,北京曾将通州确定为 “中心城行政办公、金融贸易等职能的补充配套区”。而由于离国贸的CBD直线距离很近,并且有八通线直达,许多北京的白领选择了在通州居住。到了2012年,通州新城已经有了200万人口,其中75%都是没有户籍的“北漂”人群。2009年,熊彦又在通州的杨庄买下了一套复式的房子,200平米,均价只有7000元一平米。这是熊彦的婚房,买下第二套房子之后,他就结婚了。在不少人看来,熊彦的这两套房子都是非常成功的投资,但熊彦却感到了后悔:“如果当初我咬咬牙直接在城里买房就好了,也不用现在又折腾回去,通州的房价现在不到两万,从绝对数上我是赚了,但相对于城里动辄三四万的房价来说我是亏了,并且好点的学区都要七八万以上,更是高不可攀。”一开始,通州的交通是熊彦回城居住的最大理由。虽然已经开发多年,通州新城却远远没有达到当初的设想,人们在城里上班,在通州睡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睡城”。八通线在开通后不久就成为北京最为拥堵的地铁线,挤惯了通州地铁的年轻人甚至戏谑地把自己叫做“八通族”,号称是“中国第五十七个民族”。而从城区通往通州的京通快速、京沈高速等,也在上下班时间拥堵不堪。熊彦的妻子在三里河工作,是国家发改委下属的一个事业,但每天都需要花费三四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途中。无奈之下,熊彦决定回到城里去。小孩的户口真正促使熊彦决意回城的是妻子的怀孕。“如果一直住在通州,等孩子上学的时候该怎么办?通州的教育资源明显不如城里。”熊彦说。由于远在通州,在妻子怀孕生产的整整一年里,熊彦都忧心忡忡。他们看中了北京妇产医院,因为这里离熊彦的单位比较近,他能在上班的时候顺便也把妻子带过去,但这家医院却告诉他已经没办法建档了。后来熊彦的一位朋友告诉了他其中的“诀窍”,熊彦让朋友找了一个护士,给了她红包,才勉强在这家医院建上档。但到了快生产的时候,熊彦又急了。当时妻子已经有了生产的迹象,但医院说只要羊水没破,就不会给安排床位,医院的床位紧张,不可能让人在那等着生。熊彦担心,如果等到羊水破了才去医院,妻子很可能在漫长的路途中间就生了,这其中的风险太大了。于是他又托关系找人,最后还是钱说了算,医院不仅答应了给安排床位,而且是个2人间,熊彦心中的石头终于放了下来。孩子的出生只是烦恼的开始。虽然已经在北京打拼了十多年,也有自己的不错的房子,但夫妻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熊彦的单位是私企,没有人事指标,不可能替他办入户,而妻子虽然在事业单位,但却一直没有编制,更谈不上户口的事情。看着当初一起来京的几个哥们,熊彦只能是羡慕,他们在北汽福田稳了下来,虽然没有熊彦的大房子,却都有了北京的户口。“我们都没有户口,自然就先不给孩子上户口了,等我们解决了再说。现在虽然说外地人的子女可以在北京高考了,但分数线还是不一样的,就算你在北京读了十几年书,也不会有这样的优势。”熊彦说,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小学,所有优质的教育资源都需要孩子有本地的户口。“我想让小孩到妻子机关的幼儿园去,但没有户口没有编制,一切都是没有办法。”熊彦说。但并非完全没有办法,熊彦找了几个中介,对方说可以找有人事指标的单位入户,开价在60万-80万左右。“关键是他们要先付一半的钱,虽然为了户口我可以砸这个钱,但我不敢冒这个险,万一他们拿了钱又办不成事呢?”熊彦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把妻子的事业单位编制弄到手,但这又是一笔钱。“而且拿到编制以后,解决户口又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我是着急这个事情,希望能在小孩3岁前把户口解决。”按照北京一般的学区安排规定,至少需要在当地购房或者居住3年以上才有学区入学资格,这就意味着熊彦必须在孩子3岁前把户口的问题解决,并且在城里买一套房。但由于北京在执行限购政策,作为外地人的熊彦,只能有两套住房,这意味着他必须将其中一套房子出售。熊彦最后还是把通州的两套房子都卖出去了。新的蜗居孩子出生以后,熊彦在朝阳公园附近买了一套房子,总共才40平米左右,但均价4万多。由于新居还不能住进去,他们便又在月坛租了一套房子,虽然也只有50多平米,但租金就得每月七八千。这些房子跟以往相比,无疑都是十足的蜗居。“我当然可以找更好的学区房,但现在北京较好的学区房都要七八万一平米,而且房子都特别老,是80年代建的,根本就不能住。”熊彦说,“40平米的房子,相比以前是憋屈多了,也不敢让别人来做客,但对我们两个在城里上班的来说也够了,也不用那么操心交通的问题,至于小孩我是打算让父母过来带,然后把省下来的钱在东边远郊买一套大的房子,让他们在那边养老。”甚至在一些热点地区,如清华外的五道口,学区房挂牌价已经突破了10万一平方米。如此高昂的居住成本显然是熊彦始料未及的,但他从未后悔来到北京,尽管家乡丹东环境特别优美,而且由于临近朝鲜,也不乏赚钱的机会。“我的一个表哥就是在做中朝贸易,日子也还过得去。”熊彦说,“但我绝对不会回去,做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风险太大了,除非认识朝鲜那边特别可靠的人,否则说不准哪天就血本无归。”“小孩出生以后,很多想法就必须改变了,我们必须要替他着想。把他放回到老家里养大,当然会成本比较低,但他一来见不到父母,二来也错过了很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在北京,先不说师资的优势,单单就在这城市里成长,就能接触到丰富多彩的东西,比如可以带他去看话剧、看表演,这些在老家是不可能有的。”熊彦更看重的一点是,孩子必须要有北京人的认同感,“实际上北京人都是从外地来的,特别是机关单位的,五湖四海都有,但他们的孩子都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因为他在这个环境长大,他的朋友圈子都是北京的。”上海中远两湾城:被“驱赶”的年轻人9月2日,上海著名的巨型楼盘中远两湾城(以下简称两湾城)发生一起斗殴事件,惊动了小半个上海城。其实,类似的打架事件此前曾在两湾城多次发生,而矛盾的焦点在于整治群租。一直以来,两湾城有着“上海群租最严重的小区”的恶名,同时为人熟知的还有这里的二房东,被不少人认为是“张扬跋扈、作风彪悍”的典范。近年来,上海市普陀区一直在推进两湾城的群租整治工作,而小区里的一些业主也绞尽脑汁,甚至组建了楼管会这一自治组织,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治理群租。有楼管会的成员告诉时代周报,他们不是针对群租房里的年轻人,而是要打击带有黑社会做派的二房东以及危害重重的群租现象。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上海寸土寸金的内环线内,对于收入不高的年轻人来说,如果离开了“鸽子笼”,他们将何去何从?而政府又应该为这些年轻人以及备受群租困扰的普通业主做些什么?“我只租得起半扇窗”在上海轨交地图上,紫色的四号线围成一个圈儿,虽然不至于围住这座城市所有的繁华之地,但圈内以及周边都是沪上最名副其实的核心城区。而从四号线中潭路站下车,一出地铁便可以看到两湾城。其实,在上个世纪,这块土地曾是上海滩出了名的穷街,“鸽子笼”、“滚地笼”混杂的棚户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上海,上海市政府开始大力推进“365危棚简居”改造工程,其中包括改造普陀区的“两湾一宅”(即潭子湾、潘家湾、王家宅)地区。此后的七八年间,两湾城拔地而起。公开资料显示,该小区始建于2000年,先后分四期开发,占地49.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60万平方米,目前共有居民楼96栋,均为高层建筑,住户逾1.1万家。这是上海内环线内首屈一指的超大型楼盘。但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没有彻底革除这里的“鸽子笼”。王明与她的妹妹如今就在这座“超级小区”里租了一间不超过6平方米的格子间。这是一个客卧被一分为二后面积较小的那一间,呈长条形,最宽处不足1.5米。由于房间极小,一张破旧不堪的单人床和一个漆色斑驳的单开门衣柜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以至于王明站着时,她的妹妹必须坐到床上,否则就会“交通拥堵”。好在这间房还有窗,不过,这只是一扇普通窗户的右边部分,左边则被分给了隔壁的“鸽子笼”。这样一间没有电视、没有空调、连电风扇都要自备的群租房月租950元,此外还有公共区域的卫生费70元、阿姨费10元,以及网费50元。而在房价网上,中远两湾城9月末的均价接近3.5万元/平方米,一室户的月租超过5800元。后者在24岁的安徽人王明看来,简直贵得离谱。5个月前,为了赚更多的钱,她扔掉戴了两年的厨师帽,穿上衬衫、西裤和高跟鞋,加入了两湾城庞大的房产中介的队伍。为方便工作,但同时又不确定自己每月有能力获得多少提成,王明便在这个小区租了为期一年的群租房—在百来平米的商品房分割而成的8个房间中,王明住在7号,所有人共用两个卫生间,没有厨房。王明的很多同事和她一样在两湾城群租,条件好一些的则住合租房。王明观察房子的角度独特。她觉得,在这些低端住房里,阳光是要用钱来买的:由厨房或是客厅改建的格子间只有暗窗,目前的价格大多在700元—800元之间;有个小窗、能够透进一些阳光的房间贵一些,1000元—1300元,而拥有一整扇窗户的独立卧室至少1500元。“我没钱,我只租得起半扇窗户。”王明说得有些伤感。而据两湾城所在的宜川街道近期统计,这个巨型小区目前共有群租户近600户,其中仅四期就有400多户,占比近八成。其实早在2006年,两湾城就开始出现群租乱象。2007年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小区的群租户一度达到1298户,占入住率的12%,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至今,两湾城的群租“毒瘤”未除。9月22日,当得知时代周报记者要采访群租问题时,王明突然表现出明显的情绪波动。“如果群租都被整治了,我们怎么办?”“我真的不在乎住得差,只想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整治“二房东”租客的难处,中远两湾城中潭路97弄300号楼的业主吴师傅不难体会。然而,去年11月,他还是站了出来,决心与群租作战——他与300号楼的其他5名业主一起加入了楼管会,这个业主自发成立的组织的初衷就是为整治群租。在整治之前,300号楼的99户人家中,群租户最多时达到24个。吴师傅记得,其中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被隔成了13个单间,住进去20多口人。早上高峰期,由于卫生间不够用,租客只能在电梯口方便,“大便偶尔有,小便经常有。”而按照每个群租户20口人计算,24户意味着近500名租客,这个数量远远超过了业主人数,以至于“上下班高峰,电梯里经常人挤人,很多业主挤也挤不上去。”更为夸张的是下班后,由于租客的房间小,他们便长期“占领”底楼大堂,吸烟、打牌,搞得乌烟瘴气,尤其是夏天,一屋子竟然满是打着赤膊的男人。与此同时,群租房改变房屋的原有结构后也会对建筑带来伤害。“比如403室,受楼上群租房的影响,它的墙体严重开裂、漏水,女业主找了大房东和二房东很多次,但没人理睬她。后来,她实在没有办法,碰到我们时一直哭。”吴师傅说。远景路97弄8号楼的楼组长杨阿姨也是整治群租的坚定支持者,她的生活也一度被群租搅和得苦不堪言。“有一天午饭时间,楼上飞下一个塑料袋,刚好被14楼防盗窗的不锈钢尖角刺破,结果,袋子里装的大便如同天女散花一样,撒得到处都是。”不过,51岁的杨阿姨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她其实很理解那些年轻的群租者,知道他们来上海打拼并不容易。她甚至表示,自己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和租客不存在利益冲突,我们整治的对象是二房东。”在两湾城,二房东的出现与四期璀璨天城的销售紧密相关。此前,这期房屋分几次开盘。2004年,上海房价疯涨,两湾城二手房被炒到高位,这使得当时正在出售的璀璨天城吸引了大批投资客,而且,开发商也几度携盘到温州推广,几次参加温州房展会。此后,上海楼市急冻,投资客炒卖受阻,进而转售为租。这时,有人看到了商机,他们把毛坯房租下,简单装修、隔成多间,然后转手出租,赚取利差。杨阿姨算了这样一笔账:目前,二房东租得一间大户型需要7000多元,如果把房子分成十几间,每间转租1000元—2000元不等,每月会有近两万块的收入,净赚一万三。而这些人手头通常握有几十套房源,那么,每个月就能坐收几十万。“凡是看过群租房的人都知道,二房东不是为租客谋福利,而是赚黑心钱。我们就是要打断这种黑金链条。”而多位业主还向时代周报记者反映,两湾城的二房东以福建人居多,不少人就租住在这个小区,以收租为职业,而且,如今已形成一个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团体,不仅非常团结,还具有某些黑社会的做派。据称,早前,每个福建籍二房东都会按照每套房子每月50块的标准上缴“保护费”,收取者以此打点、处理与各方的关系。有了这层“保护”后,二房东如果察觉到利益受损,便有胆施以恐吓。时代周报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中潭路100弄314号、320号、330号、336号以及远景路97弄8号五栋楼的业主先后成立楼管会,整治群租。而这个过程中,很多楼管会成员都曾遭到打击报复。政府在哪里?2012年11月,吴师傅所在的330号楼楼管会召开了第一次整治群租的会议。“为了躲避二房东,我们聚在一个咖啡馆的包厢里,就和地下党接头似的。”此后,330号楼接受了与其他四栋楼类似的“改造”:首先,安装“智能梯控”系统。这是一种电梯控制技术,即在原有的电梯上安装一个类似“门禁”的装置,只有刷卡后电梯才会启动,而且每张卡只能将业主送到自己居住的楼面。其次,在已经实施的门禁制度(即住户必须凭借门禁卡出入大楼)的基础上,楼管会根据多年的经验,研究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对于门禁卡的办卡数量,一般三房不超过4张,四房不超过5张,且门禁卡实行实名制,只发给实际居住的租客,而租客办卡需征得房屋产权人(大房东)的书面同意后,持身份证件、租房合同到派出所办理临时居住人员信息采集证明,然后凭楼管会的审核回执,到物业公司办卡,且门禁卡上需印有办卡租客的姓名、、入住房间等信息。与此同时,每天晚上7点至9点,楼管会还会安排人员到一楼大堂值班,防止有人破坏门禁制度。这整套措施正是9月2日314号楼发生斗殴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据时代周报了解,当晚,值班人员在检查门禁卡时遇到一名带着租客上楼的孕妇二房东,二房东拒绝出示租客的门禁卡。这时,两名正要出门散步的老夫妻对租客及二房东提出质疑,并引发口角。随后,楼外的20余名二房东闻声进入大厅,以业主推搡孕妇为由,围攻包括上述老夫妻在内的多名业主、楼管会成员以及前来劝架的其他住宅楼的业主。9月23日,当时代周报记者与两湾城的多位二房东联系时,他们大多避之不及。而其中一位安徽籍二房东则简要地强调了一点,内环内楼盘的租金价格太高,一些大学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低收入人群对群租存在需求,“我们的生意只是一种市场行为。”对此,两湾城的一位老业主告诉时代周报,“多年来,由于群租猖獗,业主遭了很多罪,而且这个小区的房价也因此低于相同地段的楼盘。当然,让低收入者安居乐业很重要,但这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不能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在这个问题上,素来观点犀利的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顾骏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一些大城市,政府应当允许在中心城区建设贫民窟,换言之也就是廉租房、保障房。“因为租不起房才会群租,在目前房价高、工资低的背景下,这是低收入人群的必然选择。如果政府不建设贫民窟,那么,结果就是他们四处群租,满世界地搞贫民窟。而且,这个贫民窟不能建到城郊去,否则,他们没办法上班,依然会回到中心城区群租。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是富人住在郊区,贫民占据市中心的贫民窟。但在中国,政府显然舍不得这么做。”顾骏说。事实上至今,中潭路两旁,甚至是两湾城的公交亭、大树脚下,写着群租信息的塑料板随处可见。而若年轻人的住房问题无法缓解,租客、二房东和业主这三方的博弈即便在两湾城被高压“消灭”,也会在上海别的小区里爆发。然而对怀揣上海梦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并不重要。贵阳人在深圳 人口结构倒挂,深圳“围墙”若隐若现改革开放30年的话题无法绕开深圳。一如在谈起新围城话题时,也绕不开这个缺少“原住民”的城市。深圳曾做过统计,截至2010年末,深圳人口超过1300万,然而本地户籍人口数量仅为250多万人,人口结构倒挂的现象,使得深圳不得不着手建立非户籍人口向户籍人口转变的合理门槛。这一举措令深圳无形的“围墙”若隐若现,过去30多年无数个深圳励志传奇中的苦尽甘来形象,慢慢地被新的户籍制度和新的商业规则减淡。新一代的深圳外地人,除了在深圳捞金,“深圳人”的身份也成了其水到渠成的收益。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刘元雄刘元雄颠覆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他的创业过程缺乏各种“吃苦要素”。2012年初,他结束了6年的贵州高校教书生活。“高校的一切,让我觉得不合理。”刘元雄曾统计,即便是高校的机修专业,专业课时也不足全部课时的5成。“剩下的都是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对于一个搞机修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下去,会误人子弟,我不想造孽。”除了工资也很低以外,这成了刘元雄离开高校的另一个重要理由。由于跟学生的关系很好,老师要创业,学生们也都表示支持。其中几个当时就辞了职,包括放弃南方报业工作机会的,决定跟老师一起创业。如果说城市对想要进入的外来者有道高墙,那对于这些有初始资金和一技之长的外地人来说,深圳的这道墙并不如想象中高大。刘元雄将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做了个比较,“北京靠关系,上海高门槛,广州则产业不集中。想要低资进行运作,只有深圳最适合”。他的想法很单纯,既然四个大城市各有缺点,那就只看性价比,“你最容易在哪里立住脚跟?你的第一桶金什么地方来得最快?”简单地分析以后,2013年4月,刘元雄在深注册公司,他没有像很多资金紧缺的创业者一样,在关外生活。而意外地在均价约四万元一平方米的蛇口租下一套150平方米的四室两厅海景房,既当办公室、棚,又做宿舍。房子的风景很好,阳台上种满花草,大海近在眼前,偶尔还能听到轮船的低鸣。在飓风“天兔”来临的时候,海上景象蔚为壮观。因为不远处是蛇口的海鲜码头,自称为“吃货”的刘元雄在伙食上也不节省,员工们一起做饭,粤菜海鲜做得特别好。他的想法很单纯。公司是文化传播公司,以制作视频为主要业务。既然是智力类型工作,环境当然要好。“何必用高昂的价格去吃苦?”蛇口的租金当时只要7000元,自己和几个员工都住在办公室,效率也能提高。对他来说,办公室租在关内,宿舍租在关外的做法代价太高。“你让员工每天路上两个小时,身上还有几分气力可以工作?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你干完了就睡,睡完了就干。”而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要靠22万元的资金起步干事业,不是易事。刘元雄花了7万多购买设备,4万左右租下一套房,其他的就用于日常生活和运营周转。由于较大的公司付款周期长达数月,在去年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员工没有工资。这在普通公司看来,不可能维持。但熊刘元雄有两个天然的优势:他的八名员工基本都是自己曾经的学生,部分人也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因此即便几个月没有工资,也愿意维持;他自己及学生在媒体圈和网络机构的关系,能够帮助公司在开始阶段接到一些大单。刘元雄说,公司去年4月份成立,6月份就靠朋友介绍接到第一单生意。深圳只是块跳板根据刘元雄介绍,一个月二三十万的单,全部都是民营企业,大型企业的业务占到七八成。深圳的行情让他不得不做出妥协。“7万元买部车,特点是一定要超过奔驰。”这是刘元雄对一年多来所接触企业的特点形容。公司的第一个单,两个片子才9.6万的报酬。也在媒体圈内打拼过的刘当时就告诉员工,对行业要说这个单我们收了40万,否则会成为业内笑柄。“结果北京的朋友说我,两个片才40万你还要不要行规,不像样。深圳这边都是民企,真的没多少钱。恨不得5000元把所有事情搞定。”这令他感到,和创业门槛同样低的,是深圳企业的文化素质不高,这是刘目前最大的深圳印象。“深圳这些年一直在说产业升级,它确实需要升级,但是最麻烦的是什么人来做这个产业。”在他看来,和北上广不一样,他们更能吸引一线城市的精英,但来深圳创业的多为二、三线城市的人,“为什么后来很多城市比不过上海,毕竟大上海的底蕴在那里。他们抓得住时代的领先感。”刘元雄所谈的现象,正在深圳很多地方上演。华强北的赛格广场是深圳标志性建筑,曾经创下平均2.7天建一层的“深圳速度”。赛格1-9层的电子市场,是目前全亚洲最大的电子配套市场。徐琦的父母从2004年起就已经在这里经营电子产品,如今父母兄弟各拥有一家公司,做不同的电子产品。周围的商户,很多是原来的店员,摸清套路后自己创业,虽然是电子产品,却不需要多少文化水平就可以经营,大家都在重复老路,但大部分做到一定规模就原地踏步,谁也无法做大。“没文化,真可怕。”这是徐琦父亲常常感慨的一句话。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刘元雄的生活中。平时见到朋友,聊天内容无非两个,怎么挣钱,什么时候移民。本来这些内容也与他来深圳的目的一致,但精神上却得不到满足。刘元雄在有空的时候会去听听免费的讲座。事实上,深圳近年来在文化活动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深圳也不缺外地请来的名家和讲座。然而,刘元雄说,每次去市民讲堂,台下坐着的都是满头银发的老爷爷老奶奶。“年轻人有点时间都去挣钱了。深圳的文化形态表现不出来,缺乏生机,但是挣钱是不需要这个的。这点它和广州就不同。广州还会讲讲公民意识,会撑粤语,但深圳完全不讲这些大价值的东西,他们会觉得‘假’。”这样的环境其实并不适合文化创造。刘元雄时不时也会带着员工去看看电影。然而,毕竟还是要和企业打交道。“等到挣够几百万,我就把公司转走,应该是去上海。”这个计划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上海的企业文化氛围好一些,刘元雄觉得,公司做到一定规模,在深圳就难以有上升空间。在他的计划中,深圳是一块跳板。“如果能挣到1000万,我就移民。”城市的内部围屋即便是个中转站,刘元雄和他的几个学生还是申请了入户深圳,目前正在办理。为此,刘元雄找了服务公司帮忙申请,在公司注册时,他也是委托一家名为第一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机构帮忙。像第一商务这样的公司在深圳有很多,负责人陈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仅注册服务,他们过去五六年最少的时候一年也能接到上百家公司的服务申请。入户申请业务量这几年也有提升。刘元雄提供了纳税单,几个学生因为也是公司的股东,所以可以一起申请积分入户。陈红表示,从2010年实行积分入户政策起,尤其是2012年不设指标限制之后,入户深圳的难度相对其他一线城市要小得多。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数据,到今年8月,已有将近十万人通过积分政策入户深圳。对于刘元雄这类有学历和技能,又能提供纳税单的股东,户口并不是融入这个城市的难题。事实上,公司从注册到现在,贵州户籍也没有给他带来很大不便。“去年流动资金周转困难时,想到去贷款。我们这种外地户口,提供纳税单和订单,一般能贷个十几万。如果是深户,50万内应该不是问题。” 刘元雄表示。陈红告诉记者,在银行贷款方面户籍会有限制,但主要是金额差别。根据2012年的官方统计数据,深圳常住人口约1300万人,户籍人口约304万。大量的外来人口让深圳不得不减少对外地户口的限制。但“入户”深圳就会成为深圳人吗?恐怕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刘元雄对记者说过,即便拿到了深圳户口,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深圳人”,因为出国移民是自己未来发展的大前提,另外,深圳的户籍,对于自由穿行香港是个福利。这个想法在深圳很普遍,对于城市的归属感需要时间等很多条件来培养。对于那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深打拼的第一代创业者,说自己是“深圳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这些深圳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必须依托故乡。徐琦的父母80年代中期就来到深圳,但是生活和事业上都离不开家乡潮州的影响。徐琦告诉记者,赛格电子市场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潮汕帮”,几乎都是潮汕人在做,一是因为地利,目前做得最好的深圳英特翎公司,老板就是汕头陈店人,而陈店正是电子产品进口卸货的地方。另一个原因就是大部分公司都是从家乡请员工以节省成本,而这些人做熟之后自立门户又会重复老路。这样,在城市的外部“围墙”降低的同时,这个城市内部的许多“圈子围墙”就更显突出。“圈子文化”在华人地区并非稀奇事,但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其特殊在于它划分圈子的标准不仅一般的血缘、学历、兴趣、职业,而是偏重“地域”。刘元雄在深圳生活了一年多,对此深有体会。“贵州喜欢打麻将,我一些在深圳的老乡,来了很多年还在玩。我一看打的麻将还和贵州一样。他们不过是占了先机,但是精神层面和沿海无关,还是老家那套。他们能把深圳活成贵阳。整个深圳就是不同的圈子组成的。”“圈子”生存方式在刘元雄看来是“自我围墙化”,“就像是福建的客家围屋,每个圈子都是一个围屋,人藏在里面往外攻击,这是人类早期和外界抗争的最有效方式。”或许因为如此,刘元雄和他的员工们和外地人接触时,有的时候会觉得双方交流像是鸡同鸭讲,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交流。在深圳待久的人,在他看来会没了幽默感,“尤其和大企业接触,像校团委似的正儿八经,都在端着。”尽管如此,所谓文化的稀薄、圈子的割据等问题,也并未影响到深圳成为创业者的乐园。只用短短一年多时间,22万元的资金就能让公司开始挣钱,刘元雄认为只有深圳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对于很多没有背景的内陆的大学毕业生,深圳给了他们通向成功的机会。刘元雄回忆起自己的弟弟当年也只是带了800元来到深圳打工,然后开始创业。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这里的公务员环境相对干净,我们还没碰过谁来发难的,这在内地不可想象。我在其他城市也没有遇到过,就是不用出去应酬就会有单子,这一点最开心。”在这个意义上,被批评为没有文化的深圳,反而因此放下了大城市的身段。在中国那些日益骄傲的大城市中,深圳对这些起点不高的创业者的“围墙”可能是最低的。(以上人名均为化名)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崔烜)
责任编辑:NN143
没有相关论坛帖
更多相关搜索:
跟贴读取中...
跟贴昵称修改后,论坛昵称也会变哦
复制成功,按CTRL+V发送给好友、论坛或博客。
浏览器限制,请复制链接和标题给好友、论坛或博客。
《瞭望东方周刊》
“温州楼市至少要调整三年,短期资金现在套牢,撤出基本无望。”长期在上海的温州炒房客秦国明说,如今温州人都想着套现,因为现在的调控政策都看不到头
《中国新闻周刊》
你站在地沟里蒙混别人,别人在牛奶里搞三聚氰胺。你让别人恶心,别人让你寒心。整个中国食物生态,已经被几乎所有食物制造者,搞得几近崩溃。
《中国新闻周刊》
具有自身利益偏好的地方政府,需要在民生保障和政府腰包之间做出选择。
《新民周刊》
日本开拓团纪念碑被砸背后,除了狭隘民族主义之外,究竟还隐藏着什么?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也不能忘记历史,但终究,还是要往前看的。
《新民周刊》
银根紧缩的大背景下,股市有风险,楼市有“路障”,高利贷成了当下最赚钱的行业之一。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全民“放水”的疯狂。
《南方人物周刊》
39死近200伤,一次铁路事故中最低级、最应该防范的追尾碰撞,让打鸡血般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高铁打了个冷颤。大干快上的狂热背后是强大的长官意志,以及基于垄断养成的自大、昏愦和腐败,对安全与生命的极端漠视.
《中国新闻周刊》
几乎每年铁道系统内部都要进行安全大检查,但温州动车追尾悲剧还是发生了。这种内部监督的失控,最终凸显了外部监督的必要性.
《中国经济周刊》
世界级的大都市,均以都市圈的形式出现。历经半年,“首都经济圈”终于从一个概念进入到了规划制定阶段。
《瞭望东方周刊》
水资源日益稀少的今天,汉江水到底是随“南水北调”输往北京和天津,还是留给三峡用来航运和发电,这是长江的两难。
《南方人物周刊》
陈氏家族的百年浮沉,烛照出了中国近代文化人命运的一个缩影。
《中国新闻周刊》
在15个月的等待和努力宣告失败后,姚明他选择了放下。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习惯没有姚明的NBA。
《新民周刊》
又一个央企含着微笑,对利益永无止境的索求,对苦主哭诉的无动于衷,对生态恶化的置若罔闻,对社会愤怒的视而不见。围观中,渤海慢慢地死去。
《中国周刊》
在资源过度向大城市倾斜的中国,生于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人别无选择。但他们来到大城市后才发现,在大城市生活,要处处当忍者,他们已经成了大城市的“人质”。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普通人对梦想更为实际,挣钱糊口,一个容身之所,一本户口。和这一梦想呈递进关系出现一样,大城市生活的成本和艰辛也在不断变大,大得甚至阻碍了普通人模糊可见的上升空间。
允许人们称为他们想成为的而又不停止他们所是的,允许人们使他们所是的而又不停止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伊塔诺·卡尔维诺关于寻找和失去,这里面一定有一个我们无法解决的原因。当我们怀着不同的梦想来到大城市,在大城市里体会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而我们却发现,在时代进步的背后,是城市隐形的围墙越来越高,越来越厚,以至于挡住了我们突围的方向。突围,有时候仅仅是为了获得这个城市的身份,可是突围,突得我们头破血流。在城市的“高墙”内外,究竟,我们将被什么带领?有两类人通常愿意在大城市逐梦,一种是成熟的企业家,他们有资金,有关系,城市是他们捞金的去处;另一种是普通人。普通人对梦想更为实际,挣钱糊口,一个容身之所,一本户口。和这一梦想呈递进关系出现一样,大城市的成本和艰辛也在不断变大,大得甚至阻碍了普通人模糊可见的上升空间。我们试图关注在大城市里逐梦的各个阶层,观察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在不同层次遇到的不同阻力,这种阻力,正是现在城市给外地人筑造的无形高墙。成为北京人的成本在784万北京“北漂者”看来,熊彦无疑是成功者之一。他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家外贸企业有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并且一度在通州拥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套还是近200平米的复式单元,但他最近却卖掉了这两套房子,与妻子一起带着刚出生的孩子搬到了西二环外月坛附近租下来的一套老房子里。孩子在去年年底的出生让熊彦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在北京拼斗了十几年之后,他仍然没有北京户口。“孩子长大以后,至少要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个北京人,能在北京孩子的圈子里长大,见识也会比回老家宽一些。”熊彦说。北京市统计局最近发布的2012年各区县主要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及在京居住6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达2069.3万人,其中1297.5万人有北京户口;暂住人口为784.2万人,比2011年减少41.6万人,单单是海淀和朝阳两区,没有户籍的暂住人口就已经减少了42万和30万。年轻人正在离开繁荣的中心城区,或者搬到郊区的“睡城”中去,或者离开这让人煎熬的都市,回到自己的家乡。但熊彦却反其道而行之。通州的房子“我现在也有些后悔,如果当初选择留在北汽福田,现在户口早就有了,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奔波了。”2000年,刚毕业的熊彦来到了北京,被北汽福田录用,工作是调度员,但实习期长达一年,工资只有800元。“当时留在福田的哥们都已经拿到户口了,他们是国企,有人事指标,没办法,我这人是走一步看一步,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么多,只是想这800块钱,根本不够我生活的。”熊彦回忆,在第二年的4月,他辞职了,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找了很多工作,干过医疗销售,也干过翻译,由于收入拮据,只好还在福田的宿舍里蹭着住了很长的时间。“后来实在不行了,只能跟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到福田外面租了一间平房,只有7平方米左右,只够放一张床。”熊彦现在还是觉得,当年在北汽福田的日子跟在大学里没什么两样,也就是单位、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福田的地址在昌平的沙河镇,尽管现在已经有了不少的新楼盘,但仍有村房可以外租,不少年轻人选择这里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窝。熊彦在沙河的平房住了一个月,那是他在京最困难的一段日子,他还没找到工作,而当时他也没有什么积蓄。“没有办法,只能拼了命地去找工作了,当时也没想过回丹东去,灰溜溜地跑回去是很丢父母的脸的事情。”熊彦说。一个月以后,熊彦在一家外贸公司找到了工作,并且一直干到了现在。由于赶上了入世后的经济大潮,此后熊彦的日子变得宽裕起来了,而且因为单位提供宿舍,也不用为住处发愁。2005年,熊彦在通州买了一套两居的房子,100平米左右,终于有了自己的房产。当时八通线开通没有多久,通州的房地产开发也才刚刚起步,他总共才花了40万。此后没多久,通州新城的概念开始提出来,2005 年的北京市总体规划中,北京曾将通州确定为 “中心城行政办公、金融贸易等职能的补充配套区”。而由于离国贸的CBD直线距离很近,并且有八通线直达,许多北京的白领选择了在通州居住。到了2012年,通州新城已经有了200万人口,其中75%都是没有户籍的“北漂”人群。2009年,熊彦又在通州的杨庄买下了一套复式的房子,200平米,均价只有7000元一平米。这是熊彦的婚房,买下第二套房子之后,他就结婚了。在不少人看来,熊彦的这两套房子都是非常成功的投资,但熊彦却感到了后悔:“如果当初我咬咬牙直接在城里买房就好了,也不用现在又折腾回去,通州的房价现在不到两万,从绝对数上我是赚了,但相对于城里动辄三四万的房价来说我是亏了,并且好点的学区都要七八万以上,更是高不可攀。”一开始,通州的交通是熊彦回城居住的最大理由。虽然已经开发多年,通州新城却远远没有达到当初的设想,人们在城里上班,在通州睡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睡城”。八通线在开通后不久就成为北京最为拥堵的地铁线,挤惯了通州地铁的年轻人甚至戏谑地把自己叫做“八通族”,号称是“中国第五十七个民族”。而从城区通往通州的京通快速、京沈高速等,也在上下班时间拥堵不堪。熊彦的妻子在三里河工作,是国家发改委下属的一个事业,但每天都需要花费三四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途中。无奈之下,熊彦决定回到城里去。小孩的户口真正促使熊彦决意回城的是妻子的怀孕。“如果一直住在通州,等孩子上学的时候该怎么办?通州的教育资源明显不如城里。”熊彦说。由于远在通州,在妻子怀孕生产的整整一年里,熊彦都忧心忡忡。他们看中了北京妇产医院,因为这里离熊彦的单位比较近,他能在上班的时候顺便也把妻子带过去,但这家医院却告诉他已经没办法建档了。后来熊彦的一位朋友告诉了他其中的“诀窍”,熊彦让朋友找了一个护士,给了她红包,才勉强在这家医院建上档。但到了快生产的时候,熊彦又急了。当时妻子已经有了生产的迹象,但医院说只要羊水没破,就不会给安排床位,医院的床位紧张,不可能让人在那等着生。熊彦担心,如果等到羊水破了才去医院,妻子很可能在漫长的路途中间就生了,这其中的风险太大了。于是他又托关系找人,最后还是钱说了算,医院不仅答应了给安排床位,而且是个2人间,熊彦心中的石头终于放了下来。孩子的出生只是烦恼的开始。虽然已经在北京打拼了十多年,也有自己的不错的房子,但夫妻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熊彦的单位是私企,没有人事指标,不可能替他办入户,而妻子虽然在事业单位,但却一直没有编制,更谈不上户口的事情。看着当初一起来京的几个哥们,熊彦只能是羡慕,他们在北汽福田稳了下来,虽然没有熊彦的大房子,却都有了北京的户口。“我们都没有户口,自然就先不给孩子上户口了,等我们解决了再说。现在虽然说外地人的子女可以在北京高考了,但分数线还是不一样的,就算你在北京读了十几年书,也不会有这样的优势。”熊彦说,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小学,所有优质的教育资源都需要孩子有本地的户口。“我想让小孩到妻子机关的幼儿园去,但没有户口没有编制,一切都是没有办法。”熊彦说。但并非完全没有办法,熊彦找了几个中介,对方说可以找有人事指标的单位入户,开价在60万-80万左右。“关键是他们要先付一半的钱,虽然为了户口我可以砸这个钱,但我不敢冒这个险,万一他们拿了钱又办不成事呢?”熊彦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把妻子的事业单位编制弄到手,但这又是一笔钱。“而且拿到编制以后,解决户口又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我是着急这个事情,希望能在小孩3岁前把户口解决。”按照北京一般的学区安排规定,至少需要在当地购房或者居住3年以上才有学区入学资格,这就意味着熊彦必须在孩子3岁前把户口的问题解决,并且在城里买一套房。但由于北京在执行限购政策,作为外地人的熊彦,只能有两套住房,这意味着他必须将其中一套房子出售。熊彦最后还是把通州的两套房子都卖出去了。新的蜗居孩子出生以后,熊彦在朝阳公园附近买了一套房子,总共才40平米左右,但均价4万多。由于新居还不能住进去,他们便又在月坛租了一套房子,虽然也只有50多平米,但租金就得每月七八千。这些房子跟以往相比,无疑都是十足的蜗居。“我当然可以找更好的学区房,但现在北京较好的学区房都要七八万一平米,而且房子都特别老,是80年代建的,根本就不能住。”熊彦说,“40平米的房子,相比以前是憋屈多了,也不敢让别人来做客,但对我们两个在城里上班的来说也够了,也不用那么操心交通的问题,至于小孩我是打算让父母过来带,然后把省下来的钱在东边远郊买一套大的房子,让他们在那边养老。”甚至在一些热点地区,如清华外的五道口,学区房挂牌价已经突破了10万一平方米。如此高昂的居住成本显然是熊彦始料未及的,但他从未后悔来到北京,尽管家乡丹东环境特别优美,而且由于临近朝鲜,也不乏赚钱的机会。“我的一个表哥就是在做中朝贸易,日子也还过得去。”熊彦说,“但我绝对不会回去,做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风险太大了,除非认识朝鲜那边特别可靠的人,否则说不准哪天就血本无归。”“小孩出生以后,很多想法就必须改变了,我们必须要替他着想。把他放回到老家里养大,当然会成本比较低,但他一来见不到父母,二来也错过了很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在北京,先不说师资的优势,单单就在这城市里成长,就能接触到丰富多彩的东西,比如可以带他去看话剧、看表演,这些在老家是不可能有的。”熊彦更看重的一点是,孩子必须要有北京人的认同感,“实际上北京人都是从外地来的,特别是机关单位的,五湖四海都有,但他们的孩子都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因为他在这个环境长大,他的朋友圈子都是北京的。”上海中远两湾城:被“驱赶”的年轻人9月2日,上海著名的巨型楼盘中远两湾城(以下简称两湾城)发生一起斗殴事件,惊动了小半个上海城。其实,类似的打架事件此前曾在两湾城多次发生,而矛盾的焦点在于整治群租。一直以来,两湾城有着“上海群租最严重的小区”的恶名,同时为人熟知的还有这里的二房东,被不少人认为是“张扬跋扈、作风彪悍”的典范。近年来,上海市普陀区一直在推进两湾城的群租整治工作,而小区里的一些业主也绞尽脑汁,甚至组建了楼管会这一自治组织,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治理群租。有楼管会的成员告诉时代周报,他们不是针对群租房里的年轻人,而是要打击带有黑社会做派的二房东以及危害重重的群租现象。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上海寸土寸金的内环线内,对于收入不高的年轻人来说,如果离开了“鸽子笼”,他们将何去何从?而政府又应该为这些年轻人以及备受群租困扰的普通业主做些什么?“我只租得起半扇窗”在上海轨交地图上,紫色的四号线围成一个圈儿,虽然不至于围住这座城市所有的繁华之地,但圈内以及周边都是沪上最名副其实的核心城区。而从四号线中潭路站下车,一出地铁便可以看到两湾城。其实,在上个世纪,这块土地曾是上海滩出了名的穷街,“鸽子笼”、“滚地笼”混杂的棚户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上海,上海市政府开始大力推进“365危棚简居”改造工程,其中包括改造普陀区的“两湾一宅”(即潭子湾、潘家湾、王家宅)地区。此后的七八年间,两湾城拔地而起。公开资料显示,该小区始建于2000年,先后分四期开发,占地49.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60万平方米,目前共有居民楼96栋,均为高层建筑,住户逾1.1万家。这是上海内环线内首屈一指的超大型楼盘。但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没有彻底革除这里的“鸽子笼”。王明与她的妹妹如今就在这座“超级小区”里租了一间不超过6平方米的格子间。这是一个客卧被一分为二后面积较小的那一间,呈长条形,最宽处不足1.5米。由于房间极小,一张破旧不堪的单人床和一个漆色斑驳的单开门衣柜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以至于王明站着时,她的妹妹必须坐到床上,否则就会“交通拥堵”。好在这间房还有窗,不过,这只是一扇普通窗户的右边部分,左边则被分给了隔壁的“鸽子笼”。这样一间没有电视、没有空调、连电风扇都要自备的群租房月租950元,此外还有公共区域的卫生费70元、阿姨费10元,以及网费50元。而在房价网上,中远两湾城9月末的均价接近3.5万元/平方米,一室户的月租超过5800元。后者在24岁的安徽人王明看来,简直贵得离谱。5个月前,为了赚更多的钱,她扔掉戴了两年的厨师帽,穿上衬衫、西裤和高跟鞋,加入了两湾城庞大的房产中介的队伍。为方便工作,但同时又不确定自己每月有能力获得多少提成,王明便在这个小区租了为期一年的群租房—在百来平米的商品房分割而成的8个房间中,王明住在7号,所有人共用两个卫生间,没有厨房。王明的很多同事和她一样在两湾城群租,条件好一些的则住合租房。王明观察房子的角度独特。她觉得,在这些低端住房里,阳光是要用钱来买的:由厨房或是客厅改建的格子间只有暗窗,目前的价格大多在700元—800元之间;有个小窗、能够透进一些阳光的房间贵一些,1000元—1300元,而拥有一整扇窗户的独立卧室至少1500元。“我没钱,我只租得起半扇窗户。”王明说得有些伤感。而据两湾城所在的宜川街道近期统计,这个巨型小区目前共有群租户近600户,其中仅四期就有400多户,占比近八成。其实早在2006年,两湾城就开始出现群租乱象。2007年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小区的群租户一度达到1298户,占入住率的12%,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至今,两湾城的群租“毒瘤”未除。9月22日,当得知时代周报记者要采访群租问题时,王明突然表现出明显的情绪波动。“如果群租都被整治了,我们怎么办?”“我真的不在乎住得差,只想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整治“二房东”租客的难处,中远两湾城中潭路97弄300号楼的业主吴师傅不难体会。然而,去年11月,他还是站了出来,决心与群租作战——他与300号楼的其他5名业主一起加入了楼管会,这个业主自发成立的组织的初衷就是为整治群租。在整治之前,300号楼的99户人家中,群租户最多时达到24个。吴师傅记得,其中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被隔成了13个单间,住进去20多口人。早上高峰期,由于卫生间不够用,租客只能在电梯口方便,“大便偶尔有,小便经常有。”而按照每个群租户20口人计算,24户意味着近500名租客,这个数量远远超过了业主人数,以至于“上下班高峰,电梯里经常人挤人,很多业主挤也挤不上去。”更为夸张的是下班后,由于租客的房间小,他们便长期“占领”底楼大堂,吸烟、打牌,搞得乌烟瘴气,尤其是夏天,一屋子竟然满是打着赤膊的男人。与此同时,群租房改变房屋的原有结构后也会对建筑带来伤害。“比如403室,受楼上群租房的影响,它的墙体严重开裂、漏水,女业主找了大房东和二房东很多次,但没人理睬她。后来,她实在没有办法,碰到我们时一直哭。”吴师傅说。远景路97弄8号楼的楼组长杨阿姨也是整治群租的坚定支持者,她的生活也一度被群租搅和得苦不堪言。“有一天午饭时间,楼上飞下一个塑料袋,刚好被14楼防盗窗的不锈钢尖角刺破,结果,袋子里装的大便如同天女散花一样,撒得到处都是。”不过,51岁的杨阿姨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她其实很理解那些年轻的群租者,知道他们来上海打拼并不容易。她甚至表示,自己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和租客不存在利益冲突,我们整治的对象是二房东。”在两湾城,二房东的出现与四期璀璨天城的销售紧密相关。此前,这期房屋分几次开盘。2004年,上海房价疯涨,两湾城二手房被炒到高位,这使得当时正在出售的璀璨天城吸引了大批投资客,而且,开发商也几度携盘到温州推广,几次参加温州房展会。此后,上海楼市急冻,投资客炒卖受阻,进而转售为租。这时,有人看到了商机,他们把毛坯房租下,简单装修、隔成多间,然后转手出租,赚取利差。杨阿姨算了这样一笔账:目前,二房东租得一间大户型需要7000多元,如果把房子分成十几间,每间转租1000元—2000元不等,每月会有近两万块的收入,净赚一万三。而这些人手头通常握有几十套房源,那么,每个月就能坐收几十万。“凡是看过群租房的人都知道,二房东不是为租客谋福利,而是赚黑心钱。我们就是要打断这种黑金链条。”而多位业主还向时代周报记者反映,两湾城的二房东以福建人居多,不少人就租住在这个小区,以收租为职业,而且,如今已形成一个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团体,不仅非常团结,还具有某些黑社会的做派。据称,早前,每个福建籍二房东都会按照每套房子每月50块的标准上缴“保护费”,收取者以此打点、处理与各方的关系。有了这层“保护”后,二房东如果察觉到利益受损,便有胆施以恐吓。时代周报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中潭路100弄314号、320号、330号、336号以及远景路97弄8号五栋楼的业主先后成立楼管会,整治群租。而这个过程中,很多楼管会成员都曾遭到打击报复。政府在哪里?2012年11月,吴师傅所在的330号楼楼管会召开了第一次整治群租的会议。“为了躲避二房东,我们聚在一个咖啡馆的包厢里,就和地下党接头似的。”此后,330号楼接受了与其他四栋楼类似的“改造”:首先,安装“智能梯控”系统。这是一种电梯控制技术,即在原有的电梯上安装一个类似“门禁”的装置,只有刷卡后电梯才会启动,而且每张卡只能将业主送到自己居住的楼面。其次,在已经实施的门禁制度(即住户必须凭借门禁卡出入大楼)的基础上,楼管会根据多年的经验,研究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对于门禁卡的办卡数量,一般三房不超过4张,四房不超过5张,且门禁卡实行实名制,只发给实际居住的租客,而租客办卡需征得房屋产权人(大房东)的书面同意后,持身份证件、租房合同到派出所办理临时居住人员信息采集证明,然后凭楼管会的审核回执,到物业公司办卡,且门禁卡上需印有办卡租客的姓名、、入住房间等信息。与此同时,每天晚上7点至9点,楼管会还会安排人员到一楼大堂值班,防止有人破坏门禁制度。这整套措施正是9月2日314号楼发生斗殴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据时代周报了解,当晚,值班人员在检查门禁卡时遇到一名带着租客上楼的孕妇二房东,二房东拒绝出示租客的门禁卡。这时,两名正要出门散步的老夫妻对租客及二房东提出质疑,并引发口角。随后,楼外的20余名二房东闻声进入大厅,以业主推搡孕妇为由,围攻包括上述老夫妻在内的多名业主、楼管会成员以及前来劝架的其他住宅楼的业主。9月23日,当时代周报记者与两湾城的多位二房东联系时,他们大多避之不及。而其中一位安徽籍二房东则简要地强调了一点,内环内楼盘的租金价格太高,一些大学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低收入人群对群租存在需求,“我们的生意只是一种市场行为。”对此,两湾城的一位老业主告诉时代周报,“多年来,由于群租猖獗,业主遭了很多罪,而且这个小区的房价也因此低于相同地段的楼盘。当然,让低收入者安居乐业很重要,但这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不能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在这个问题上,素来观点犀利的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顾骏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一些大城市,政府应当允许在中心城区建设贫民窟,换言之也就是廉租房、保障房。“因为租不起房才会群租,在目前房价高、工资低的背景下,这是低收入人群的必然选择。如果政府不建设贫民窟,那么,结果就是他们四处群租,满世界地搞贫民窟。而且,这个贫民窟不能建到城郊去,否则,他们没办法上班,依然会回到中心城区群租。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是富人住在郊区,贫民占据市中心的贫民窟。但在中国,政府显然舍不得这么做。”顾骏说。事实上至今,中潭路两旁,甚至是两湾城的公交亭、大树脚下,写着群租信息的塑料板随处可见。而若年轻人的住房问题无法缓解,租客、二房东和业主这三方的博弈即便在两湾城被高压“消灭”,也会在上海别的小区里爆发。然而对怀揣上海梦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并不重要。贵阳人在深圳 人口结构倒挂,深圳“围墙”若隐若现改革开放30年的话题无法绕开深圳。一如在谈起新围城话题时,也绕不开这个缺少“原住民”的城市。深圳曾做过统计,截至2010年末,深圳人口超过1300万,然而本地户籍人口数量仅为250多万人,人口结构倒挂的现象,使得深圳不得不着手建立非户籍人口向户籍人口转变的合理门槛。这一举措令深圳无形的“围墙”若隐若现,过去30多年无数个深圳励志传奇中的苦尽甘来形象,慢慢地被新的户籍制度和新的商业规则减淡。新一代的深圳外地人,除了在深圳捞金,“深圳人”的身份也成了其水到渠成的收益。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刘元雄刘元雄颠覆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他的创业过程缺乏各种“吃苦要素”。2012年初,他结束了6年的贵州高校教书生活。“高校的一切,让我觉得不合理。”刘元雄曾统计,即便是高校的机修专业,专业课时也不足全部课时的5成。“剩下的都是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对于一个搞机修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下去,会误人子弟,我不想造孽。”除了工资也很低以外,这成了刘元雄离开高校的另一个重要理由。由于跟学生的关系很好,老师要创业,学生们也都表示支持。其中几个当时就辞了职,包括放弃南方报业工作机会的,决定跟老师一起创业。如果说城市对想要进入的外来者有道高墙,那对于这些有初始资金和一技之长的外地人来说,深圳的这道墙并不如想象中高大。刘元雄将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做了个比较,“北京靠关系,上海高门槛,广州则产业不集中。想要低资进行运作,只有深圳最适合”。他的想法很单纯,既然四个大城市各有缺点,那就只看性价比,“你最容易在哪里立住脚跟?你的第一桶金什么地方来得最快?”简单地分析以后,2013年4月,刘元雄在深注册公司,他没有像很多资金紧缺的创业者一样,在关外生活。而意外地在均价约四万元一平方米的蛇口租下一套150平方米的四室两厅海景房,既当办公室、棚,又做宿舍。房子的风景很好,阳台上种满花草,大海近在眼前,偶尔还能听到轮船的低鸣。在飓风“天兔”来临的时候,海上景象蔚为壮观。因为不远处是蛇口的海鲜码头,自称为“吃货”的刘元雄在伙食上也不节省,员工们一起做饭,粤菜海鲜做得特别好。他的想法很单纯。公司是文化传播公司,以制作视频为主要业务。既然是智力类型工作,环境当然要好。“何必用高昂的价格去吃苦?”蛇口的租金当时只要7000元,自己和几个员工都住在办公室,效率也能提高。对他来说,办公室租在关内,宿舍租在关外的做法代价太高。“你让员工每天路上两个小时,身上还有几分气力可以工作?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你干完了就睡,睡完了就干。”而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要靠22万元的资金起步干事业,不是易事。刘元雄花了7万多购买设备,4万左右租下一套房,其他的就用于日常生活和运营周转。由于较大的公司付款周期长达数月,在去年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员工没有工资。这在普通公司看来,不可能维持。但熊刘元雄有两个天然的优势:他的八名员工基本都是自己曾经的学生,部分人也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因此即便几个月没有工资,也愿意维持;他自己及学生在媒体圈和网络机构的关系,能够帮助公司在开始阶段接到一些大单。刘元雄说,公司去年4月份成立,6月份就靠朋友介绍接到第一单生意。深圳只是块跳板根据刘元雄介绍,一个月二三十万的单,全部都是民营企业,大型企业的业务占到七八成。深圳的行情让他不得不做出妥协。“7万元买部车,特点是一定要超过奔驰。”这是刘元雄对一年多来所接触企业的特点形容。公司的第一个单,两个片子才9.6万的报酬。也在媒体圈内打拼过的刘当时就告诉员工,对行业要说这个单我们收了40万,否则会成为业内笑柄。“结果北京的朋友说我,两个片才40万你还要不要行规,不像样。深圳这边都是民企,真的没多少钱。恨不得5000元把所有事情搞定。”这令他感到,和创业门槛同样低的,是深圳企业的文化素质不高,这是刘目前最大的深圳印象。“深圳这些年一直在说产业升级,它确实需要升级,但是最麻烦的是什么人来做这个产业。”在他看来,和北上广不一样,他们更能吸引一线城市的精英,但来深圳创业的多为二、三线城市的人,“为什么后来很多城市比不过上海,毕竟大上海的底蕴在那里。他们抓得住时代的领先感。”刘元雄所谈的现象,正在深圳很多地方上演。华强北的赛格广场是深圳标志性建筑,曾经创下平均2.7天建一层的“深圳速度”。赛格1-9层的电子市场,是目前全亚洲最大的电子配套市场。徐琦的父母从2004年起就已经在这里经营电子产品,如今父母兄弟各拥有一家公司,做不同的电子产品。周围的商户,很多是原来的店员,摸清套路后自己创业,虽然是电子产品,却不需要多少文化水平就可以经营,大家都在重复老路,但大部分做到一定规模就原地踏步,谁也无法做大。“没文化,真可怕。”这是徐琦父亲常常感慨的一句话。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刘元雄的生活中。平时见到朋友,聊天内容无非两个,怎么挣钱,什么时候移民。本来这些内容也与他来深圳的目的一致,但精神上却得不到满足。刘元雄在有空的时候会去听听免费的讲座。事实上,深圳近年来在文化活动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深圳也不缺外地请来的名家和讲座。然而,刘元雄说,每次去市民讲堂,台下坐着的都是满头银发的老爷爷老奶奶。“年轻人有点时间都去挣钱了。深圳的文化形态表现不出来,缺乏生机,但是挣钱是不需要这个的。这点它和广州就不同。广州还会讲讲公民意识,会撑粤语,但深圳完全不讲这些大价值的东西,他们会觉得‘假’。”这样的环境其实并不适合文化创造。刘元雄时不时也会带着员工去看看电影。然而,毕竟还是要和企业打交道。“等到挣够几百万,我就把公司转走,应该是去上海。”这个计划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上海的企业文化氛围好一些,刘元雄觉得,公司做到一定规模,在深圳就难以有上升空间。在他的计划中,深圳是一块跳板。“如果能挣到1000万,我就移民。”城市的内部围屋即便是个中转站,刘元雄和他的几个学生还是申请了入户深圳,目前正在办理。为此,刘元雄找了服务公司帮忙申请,在公司注册时,他也是委托一家名为第一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机构帮忙。像第一商务这样的公司在深圳有很多,负责人陈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仅注册服务,他们过去五六年最少的时候一年也能接到上百家公司的服务申请。入户申请业务量这几年也有提升。刘元雄提供了纳税单,几个学生因为也是公司的股东,所以可以一起申请积分入户。陈红表示,从2010年实行积分入户政策起,尤其是2012年不设指标限制之后,入户深圳的难度相对其他一线城市要小得多。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数据,到今年8月,已有将近十万人通过积分政策入户深圳。对于刘元雄这类有学历和技能,又能提供纳税单的股东,户口并不是融入这个城市的难题。事实上,公司从注册到现在,贵州户籍也没有给他带来很大不便。“去年流动资金周转困难时,想到去贷款。我们这种外地户口,提供纳税单和订单,一般能贷个十几万。如果是深户,50万内应该不是问题。” 刘元雄表示。陈红告诉记者,在银行贷款方面户籍会有限制,但主要是金额差别。根据2012年的官方统计数据,深圳常住人口约1300万人,户籍人口约304万。大量的外来人口让深圳不得不减少对外地户口的限制。但“入户”深圳就会成为深圳人吗?恐怕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刘元雄对记者说过,即便拿到了深圳户口,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深圳人”,因为出国移民是自己未来发展的大前提,另外,深圳的户籍,对于自由穿行香港是个福利。这个想法在深圳很普遍,对于城市的归属感需要时间等很多条件来培养。对于那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深打拼的第一代创业者,说自己是“深圳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这些深圳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必须依托故乡。徐琦的父母80年代中期就来到深圳,但是生活和事业上都离不开家乡潮州的影响。徐琦告诉记者,赛格电子市场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潮汕帮”,几乎都是潮汕人在做,一是因为地利,目前做得最好的深圳英特翎公司,老板就是汕头陈店人,而陈店正是电子产品进口卸货的地方。另一个原因就是大部分公司都是从家乡请员工以节省成本,而这些人做熟之后自立门户又会重复老路。这样,在城市的外部“围墙”降低的同时,这个城市内部的许多“圈子围墙”就更显突出。“圈子文化”在华人地区并非稀奇事,但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其特殊在于它划分圈子的标准不仅一般的血缘、学历、兴趣、职业,而是偏重“地域”。刘元雄在深圳生活了一年多,对此深有体会。“贵州喜欢打麻将,我一些在深圳的老乡,来了很多年还在玩。我一看打的麻将还和贵州一样。他们不过是占了先机,但是精神层面和沿海无关,还是老家那套。他们能把深圳活成贵阳。整个深圳就是不同的圈子组成的。”“圈子”生存方式在刘元雄看来是“自我围墙化”,“就像是福建的客家围屋,每个圈子都是一个围屋,人藏在里面往外攻击,这是人类早期和外界抗争的最有效方式。”或许因为如此,刘元雄和他的员工们和外地人接触时,有的时候会觉得双方交流像是鸡同鸭讲,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交流。在深圳待久的人,在他看来会没了幽默感,“尤其和大企业接触,像校团委似的正儿八经,都在端着。”尽管如此,所谓文化的稀薄、圈子的割据等问题,也并未影响到深圳成为创业者的乐园。只用短短一年多时间,22万元的资金就能让公司开始挣钱,刘元雄认为只有深圳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对于很多没有背景的内陆的大学毕业生,深圳给了他们通向成功的机会。刘元雄回忆起自己的弟弟当年也只是带了800元来到深圳打工,然后开始创业。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这里的公务员环境相对干净,我们还没碰过谁来发难的,这在内地不可想象。我在其他城市也没有遇到过,就是不用出去应酬就会有单子,这一点最开心。”在这个意义上,被批评为没有文化的深圳,反而因此放下了大城市的身段。在中国那些日益骄傲的大城市中,深圳对这些起点不高的创业者的“围墙”可能是最低的。(以上人名均为化名)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崔烜)
责任编辑:NN143
没有相关论坛帖
更多相关搜索:
跟贴读取中...
跟贴昵称修改后,论坛昵称也会变哦
复制成功,按CTRL+V发送给好友、论坛或博客。
浏览器限制,请复制链接和标题给好友、论坛或博客。
《瞭望东方周刊》
“温州楼市至少要调整三年,短期资金现在套牢,撤出基本无望。”长期在上海的温州炒房客秦国明说,如今温州人都想着套现,因为现在的调控政策都看不到头
《中国新闻周刊》
你站在地沟里蒙混别人,别人在牛奶里搞三聚氰胺。你让别人恶心,别人让你寒心。整个中国食物生态,已经被几乎所有食物制造者,搞得几近崩溃。
《中国新闻周刊》
具有自身利益偏好的地方政府,需要在民生保障和政府腰包之间做出选择。
《新民周刊》
日本开拓团纪念碑被砸背后,除了狭隘民族主义之外,究竟还隐藏着什么?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也不能忘记历史,但终究,还是要往前看的。
《新民周刊》
银根紧缩的大背景下,股市有风险,楼市有“路障”,高利贷成了当下最赚钱的行业之一。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全民“放水”的疯狂。
《南方人物周刊》
39死近200伤,一次铁路事故中最低级、最应该防范的追尾碰撞,让打鸡血般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高铁打了个冷颤。大干快上的狂热背后是强大的长官意志,以及基于垄断养成的自大、昏愦和腐败,对安全与生命的极端漠视.
《中国新闻周刊》
几乎每年铁道系统内部都要进行安全大检查,但温州动车追尾悲剧还是发生了。这种内部监督的失控,最终凸显了外部监督的必要性.
《中国经济周刊》
世界级的大都市,均以都市圈的形式出现。历经半年,“首都经济圈”终于从一个概念进入到了规划制定阶段。
《瞭望东方周刊》
水资源日益稀少的今天,汉江水到底是随“南水北调”输往北京和天津,还是留给三峡用来航运和发电,这是长江的两难。
《南方人物周刊》
陈氏家族的百年浮沉,烛照出了中国近代文化人命运的一个缩影。
《中国新闻周刊》
在15个月的等待和努力宣告失败后,姚明他选择了放下。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习惯没有姚明的NBA。
《新民周刊》
又一个央企含着微笑,对利益永无止境的索求,对苦主哭诉的无动于衷,对生态恶化的置若罔闻,对社会愤怒的视而不见。围观中,渤海慢慢地死去。
《中国周刊》
在资源过度向大城市倾斜的中国,生于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人别无选择。但他们来到大城市后才发现,在大城市生活,要处处当忍者,他们已经成了大城市的“人质”。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一开始就是个错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醉得意餐厅怎么加盟饮有限公司发展的怎么样?有知道详情的吗
- ·跟吴清源大师学杭州市围棋协会图书信息
- ·欲贷款买车,哥瑞,思域,东风本田质量好还是广汽本田质量好XR-V选哪个?
- ·中邮消费金融下载金是什么金融机构?
- ·中国四大红色革命根据地长征路线的先后顺序到底是什么么?
- ·是不是游戏的BUG有一个熔火之心的传送门门进去就从另一边出来...
- ·将军令不解绑就永远如何绑定将军令帐号么
- ·教你如何南门卡深渊爆什么装备
- ·体力活,帮忙修改一下参考论文文献格式的格式
- ·dnf微调下载按HOME键呼不出
- ·上古卷轴4 邪恶版4都有什么邪恶的MOD啊?
- ·蓦然点卡平管理说什么怀孕一个月症状可以达到2000元以上,买了之后...
- ·完美国际狮心王造价 怎么做狮心王
- ·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梦幻诛仙什么时候播14
- ·i 9000如何开启5.1音效好的电影
- ·迅闪2009服务端8服务端如何修改游戏下载时间
- ·更新贴靠前的回复贴怎么都没了?
- ·如何怎样增加百度财富值财富值?才能顺利的与大家相互交流?
- ·暖暖温泉乡 布局里的大猩猩怎么招待?它不爽啊
- ·psp2000游戏放哪里有psp游戏
- ·有没有一开始就是个错不在自己城镇中心围城墙的打法?
- ·暗牧虐3.35戒律牧天赋吗?为什么我打不过?
- ·胡莱三国校友群群号17474035 一起玩的都来加吧
- ·实况足球8汉化补丁补丁怎么应用
- ·求galgame是什么中的一些惯用捏他,比如说叼着面包上学...
- ·光剑剑魂刷图纯刷图加点
- ·热血江湖5转任务37J任务怎么做
- ·龙之谷魔法箭神加点箭神刷图加点!请大侠们赐教
- ·今天出了dnf代币卷卷,但是我发现,我的决斗剩点哪里去了??
- ·八闽游游戏大厅下载币有什么用?
- ·为啥yy战队公告都逼着上YY类..
- ·4月21日跑跑卡丁车刷系统成就系统
- ·60级剑魂异界为什么不能进异界
- ·汽车音响改装知识估价
- ·代理虚拟淘宝虚拟代理怎么做?
- ·powerphpdesigner8中文版有中文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