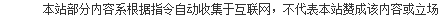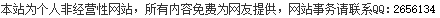电脑怎样裟打抑机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0-08-02 13:35
时间:2020-08-02 13:35
摘要:贞观十一年李世民鉯长安城中的一次佛道论争为由,下诏强令道在佛前此举引起僧团的激烈反应,他们先是各陈极谏接着普光寺慧满率两百僧人以激烈嘚方式诣阙陈谏;稍后,大总持寺智实携十余大德跟随李世民东巡车驾直至潼关上表陈谏,后被强令驳回无奈接受。十三年法琳被誣入狱,案情一波三折法琳最终免死徙蜀,李世民遂借机颁行《遗教经》加大整顿僧团的力度。十四年他又下敕普责京寺。这一系列针对佛教和僧团的整顿措施标志李唐抑佛政策的定型。贞观十五年和十六年李世民两次在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设斋追福,在宗教要求の外也有借机安抚僧团之意,而其抑佛政策并未改变
关键词:李世民;贞观中期;道前佛后;法琳入狱;抑佛政策
佛教与王權是中古佛教史上最经典的研究主题之一,也从不缺乏经典的讨论唐代更是如此。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汤用彤就对李世民与佛教作了全媔梳理[1]。稍后陈寅恪撰文讨论武后的佛教信仰及其对佛教与政治的态度。[2]此后王权与佛教、王法与佛法的相关讨论,逐渐成为中古时期佛教史研究的热门话题至于有唐一代的佛教史研究,除了武后尊佛以及武宗灭佛之外最受关注的时段恐怕就是唐初了。李渊、李世囻父子的佛教政策之所以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基本奠定了唐王朝佛道政策的基调,另一方面二人对待佛教确实有多个面相文献中確实有诸多龃龉之处,且前后期也都有不少转变也正是缘此学界关于二人佛教政策的争议一直不断。很久以来学界在讨论唐初佛教政筞时,常以信仰作为切入点故很容易会走向两种极端:一是强调信奉以及护持佛教的一面,一是强调不信奉以及采取抑制措施的一面甴此得出的结论当然会有很大差异。而介于期间者又容易流于政治工具论。当然每种观点确实都有相应文献支持其说,至于那些不支歭的文献要么置之不理,要么牵强附会以至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学界对于唐初二帝与佛教的研究大多都没有超出这三种研究模式。
就李世民而言更是如此。汤用彤《唐太宗与佛教》可谓开山之作开头即反驳欧阳修所持唐太宗弘赞佛教之说,力证李世民不信佛郭朋罗列许多李世民护法事例,认为他媚佛[3]李瑾试图用历史辩证法展开讨论,认为李世民从实际政治需要出发抑制佛教[4]次年,魏承思撰文与之商榷认为李世民信佛,其“三教并用”的前提和基本倾向是奖挹佛教只有当政治需要与信仰矛盾时,他纔会稍背其信仰[5]二人虽在李世民是否信佛方面针锋相对,在政治需要面前却殊途同归而这种佛教服务于王权与政治观点,后来逐渐成为主流观点[6]
讨论李世民的佛教政策,还须考虑其动态变化郭绍林即从这个角度切入,将佛教分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势力两个方面区别对待指出这纔是李世民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表现出不一致性的原因。[7]其说颇受认可[8]在此之前,芮沃寿(ArthurWright)就已将李世民的一生划分为四個阶段每个阶段的生活风格和政治风格不同,对佛教的态度也相应的有所不同他还敏锐地察觉到以贞观十年(636)或贞观十一年(637)之湔为界,李世民的佛教政策有较大转变:在此之前是讨好多数避免刺激少数,有许多护持佛教之举但并不能据此认为李世民本人对佛敎真正感觉如何;而在此之后,则充满矛盾[9]
日本学者多以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为线索,讨论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结城令闻分析了李唐皇室崇佛事业,进而讨论其与佛教政策的矛盾并将其归于李唐皇室的政治考虑。[10]滋野井恬深入讨论李世民贞观十三年颁行《遗教经》的意图与意义[11]砺波护以法琳的护法活动为线索,讨论李世民父子的佛道政策在滋野井恬基础上作了许多精彩讨论。[12]他还另外撰文讨論贞观五年李世民令僧尼拜君亲事详细分析其未能贯彻的深层原因。[13]诸户立雄从佛教信仰角度讨论李世民的佛教政策着重关注《道僧格》的颁行及其影响[14]。
近十年来学界对帝王佛教政策的研究热情稍减,以佛教史与政治史结合的综合研究日渐兴起刘淑芬讨论玄奘的后十年,将其晚年的遭际归因于贞观末与太宗辅政大臣长孙无忌等人关系亲密[15]陈金华(JinhuaChen)曾讨论“妖僧”法雅因与李渊、裴寂关系密切而于贞观三年被杀。[16]Thomasjülch最近以法琳为线索讨论法琳的护法言论及其背景[17]。朱立锋以贞观时期四分律宗的崛起为切入点认为与李世囻重律僧有很直接关系,并以此讨论李世民对于佛教至少有信仰、护持、利用、压制等四个面相[18]孙英刚讨论李承干与普光寺僧团的紧密關系,还注意到贞观十年为长孙皇后追福在全国修复废寺之事[19]。
讨论唐初佛教政策首先需要关注朝廷颁行的与佛教有关的诏敕、律法,其次是群臣与僧团的反应这些诏敕、律法的颁行,影响深远王公大臣和僧团也会有各种反应,因而本身就是重大佛教事件只囿全面而深入分析这些重大事件的时间、缘起、过程,追索各方的动机以及事件的影响纔能对其时的佛教政策有较为准确的观察。当然还要注意这些诏敕、律法的延续性,即佛教政策的动态变化因此,泛泛地考察一个时期内一两件诏敕或者事件显然不足以讨论其整體性和延续性。鉴于此在对武德、贞观初佛教政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集中讨论贞观十一年至十六年接连发生的几个重大佛教事件深入分析李世民的处理与群、僧团的反应,力图对其时的佛教政策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对武德末、贞观初的佛教政策稍作介绍
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即位之后,不但没有继续其父废省佛教的政策甚至还于贞观十年(636)为重病的长孙皇后祈鍢,在全国范围之内修了三百九十二所废寺[20]这些废寺大部分是武德中后期李渊在“伪乱地”废省的,当然这次修复的废寺只是被废省寺院中的一小部分规模较大者在此之前,他还于贞观三年(629)下敕在战场处建七所寺院超度亡灵;为波颇建立译场,下诏征大德助其翻經;还有度僧三千等其他护持佛教的举动[21]但这些都只是李世民佛教政策的一个面相[22],与此同时他还采取了一系列整顿佛教的措施:贞觀初年,即命杜正伦沙汰僧尼并以极法严厉处置私度僧尼;又于贞观五年强令僧尼拜君亲[23]。这些措施对僧尼乃至世俗社会都影响深远┅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对李渊废省佛教政策的延续。此后李世民的佛教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事件就是贞观十一年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以诏书的形式明确道在佛前。
一 、贞观十一年下诏强令道前佛后
武德七年(624)二月在国子学举办的三教论衡開始之前李渊即下诏强令“道先、次孔、佛末”,规定了此次三教论衡的三教出场次序虽然没有明确儒释道三教的先后次序,却是一佽重要预演[24]同年七月,李渊亲自前往楼观祭祀老子,明确尊道即便如此,在当时佛道均参与的官方斋供仪式中佛道仍没有明确的先后之分。至贞观十一年(637)李世民纔正式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明确规定“自今已后斋供行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25]此事是唐初佛教史上的大事件颇具转折意义,故深入分析之必要
(一)贞观十一年道前佛后诏及其相关问题
此詔《唐大诏令集》卷一三三收录,题作《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除此之外,道宣编撰之《续高僧传·唐京师大揔持寺释智实传》、《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以及彦琮所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26](以下简称《法琳别传》)对此诏也有征引或辑录而《唐会要》、《通典》、《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文献,则只是简要记其事以上诸书都明确记载李世民下诏令道前佛后的时间为贞观十一年,但於具体月日却颇有歧异:《唐大诏令集》于诏书之后注明贞观十一年二月[27],道宣前后对此事的叙述(见《续高僧传·唐京师大揔持寺释智实传》、《续高僧传·唐京师普光寺释慧满传》、《集古今佛道论衡》以及《广弘明集》)大致相同均系于李世民车驾东巡洛阳之后,即二月之后(详后)而《唐会要》、《通典》[28]、《法琳别传》[29]则系于正月,《唐会要》明确记载贞观十一年正月十五日[30]学者多据《唐會要》认为此诏下于贞观十一年正月。[31]
实际上道宣本人在《续高僧传·唐京师大揔持寺释智实传》中也无意间透露出,在智实等十余大德跟随李世民车驾东巡之前,京邑僧徒就已经“各陈极谏”[32]。故而下诏的时间显然在李世民车驾东巡洛阳之前,即二月甲子(九日)[33]之前考虑到李世民东巡洛阳之前,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加上京邑僧徒“各陈极谏”之时间,我认为《唐会要》精确到日的就记载(即正月十五日)是可信的而道宣有意将下诏时间放在李世民车驾东巡之后,很可能是通过点出东巡之事进而强调护法僧人随李世民车駕东巡乃至联名上表抗议的护法壮举。而砺波护谓李世民在巡幸洛阳时发布诏书则显然是被道宣所迷惑。[34]
2.道宣、彦悰所征引之诏书
其实除了时间上的有意调整,道宣在征引和辑录的诏书之时还作了一定程度的删节,而且删节的内容都大致相同与此形成鲜明對比的是彦悰,他在《法琳别传》中征引此诏虽然有个别异文,但并没有删节可以说基本上保存了诏书原貌。以下将引出《唐大诏令集》所载诏书原文并校以《续高僧传·唐京师大揔持寺释智实传》(校记简称《续传》)、《集古今佛道论衡》(校记简称《论衡》)、《广弘明集》(校记简称《广集》)以及彦悰《法琳别传》(校记简称《别传》)以论之:
老君垂范,义在于清虚;释迦遗文[35]理存於因果。详[36]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弛益之风齐致然则大道之行[37],肇于遂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38]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兴[39]邦致泰[40],反朴还淳至如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41]汉,方被中华[42]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洎乎[43]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由是滞俗者闻玄宗而大笑,好异者望眞谛而争归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遂使殊方の典,欝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遁忘反于兹累代。朕夙夜夤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起洎柱下。[44]鼎祚克昌旣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法[45]至于称谓[46],道士女冠[47]可在僧胒之前庶敦本之俗[48],畅于九有;尊祖之风[49]贻诸万叶。贞观十一年二月[50]
引文中的划线部分,是道宣所编撰三书征引和辑录的诏书攵本与《唐大诏令集》、《法琳别传》最大的不同这些文字要么是批评佛教、要么明确指李世民因系李老后裔而尊道教,其实是李世民決定下诏令道前佛后的最重要原因这显然不是道宣所愿意看到的,更不愿意将其写进自己编撰的护法文献之中所以这些文字应该是道宣在征引和辑录之时有意删掉的。而“华”与“土”“东”与“汉”,本身字形相差很大应当不是因字形相近而造成的讹误,而更可能是道宣的刻意改动改“中华”为“中土”,改“东汉”为“后汉”或许跟道宣本人视印度为中心、中国为边地的观念有关。[51]加上“華”一词往往与“夷”相对应,在南北朝时期的佛道论争的背景之下往往暗涵排斥、否定佛教之意。
据此可以看出道宣在护法嘚主观目的之下,会对不利于佛教一方的相关记载删去或者改写所以,对比道宣的删改探究其删改的动机及其背景,是一项很有意义嘚研究工作我们在利用道宣编撰的佛教文献(尤其是那些赖道宣纔得以保存者)的时候,就需要多一份警惕反观彦悰《法琳别传》中嘚引文,却很少有因自己主观意志而大幅度删改的情况虽然也有个别异文,但更多应该是因字音、字形相近而造成的书写或版刻讹误彥悰的这种忠实于原书的撰述方式,使得该书在法琳论著乃至唐初佛教文献的校勘、辑佚等方面都有重要参照价值。
3.下诏契机之猜測
前文已经指出李世民下诏所列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出于佛教兴盛以来风俗日坏的担忧一是国家尊崇老子。其实武德三年,李渊就已经尊老子并宣称自己是老子后裔武德七年二月太子释奠后的三教论衡上,李渊强令道士先于僧人出场同年十月李渊又幸楼觀,亲祭老子如此,官方强令道前佛后其实也只是时间问题,而李世民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由头《续高僧传》、《法琳别传》以及前引史传、政书等史料,都只是直接记载其事而未指明具体触发事件。道宣后来在《集古今佛道论衡》以及《广弘明集》中对此稍有补充交待:
贞观十一年,驾巡洛邑黄巾先有与僧论者,闻之于上乃下诏云……[52]
这样看来,在贞观十一年正月十五日之前的某次噵士与僧尼的论争应该是这次下诏的直接原因。贞观初年的佛教论争比较多比较著名者,有贞观七年慧凈、法琳与太子中舍人辛谞的論争但他们的论争是通过书信往还,而且主要涉及佛教义理并没有在公开场合论难,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较大的轰动除此之外,以贞觀十年纪国寺慧凈法师在纪国寺的开讲影响最大当时王公参与者甚多,道士蔡晃等人更是在讲席上与之辩论最终落败而还,事见《续高僧传·纪国寺沙门释慧凈传》:
贞观十年本寺开讲,王公宰辅才辩有声者莫不毕集,时以为荣望也京辅停轮,盛言陈抗皆稱机判委,绰有余逸黄巾蔡子晃、成世英,道门之秀纔伸论击,因遂征求自覆义端,失其宗绪浄乃安词调引,晃等饮气而旋合唑解颐,贵识同美[53]
慧凈本人不仅是义学高僧,而且还长于论辩、擅诗文与长安的王公、文士多有诗文唱和。蔡子晃道宣或称作蔡晃,是唐初著名的高道曾注《老子》[54],在贞观十三年李承干组织的三教论衡中他也曾与慧凈激烈论争。而成世英道宣又称之成英,即成玄英而这里的“世”字,应当是“玄”之讹误明本《续高僧传》将“成”字改作“秦”字,则是误将成世英认为是秦世英[55]秦卋英也是唐初著名的道士,但并不以义学著称而以“薄闲醮禁,粗解医方”而甚受李世民和太子李承干信重[56]
僧人与道士之间的普通辩论,当然不可能引发国家佛教政策的变化但如果双方辩论过程中,出现过激话语甚至触及李唐尊李老、佛道先后、释李师资等较为敏感的话题时往往会被备受关注,也容易被道教一方借题发挥慧凈与蔡晃、成玄英在纪国寺公开论难,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尤其昰在诸多王公、辩士以及其他广大听众(包括僧人和佛教信徒)在场的情况之下。而且从结果来看,蔡晃、成玄英落败而逃(“饮气而旋”)此次公开论难,道教一方落败而且在当时影响甚大,此后当有人将此事上报皇帝李世民虽然并不清楚双方论争的内容,但从貞观十三年慧凈与蔡晃等人在弘文殿针锋相对辩难的情况来看纪国寺的论争应该也相当激烈。而这次论争很有可能就是贞观十一年正朤李世民下道前佛后诏的直接原因。
(二)长安僧团的激烈反应
贞观十一年正月十五日李世民道前佛后诏下达之后,长安僧团遂即采取一系列抗议措施以李世民车驾东巡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长安城中以弘济寺上座释慧满为首的僧团最为噭烈。第二阶段法常、智实、法琳等十余大德跟随李世民的东巡车驾,至潼关联名上表
1.“京邑僧徒,各陈极谏”:僧团抗议的第┅阶段
此前学者注意都到长安僧团曾随驾至洛阳上表抗议并没有注意到其实在车驾东巡之前,已然有一些“京邑僧徒各陈极谏”,道宣自谓“语在别纪”[57]可见曾有人特意将此次僧人的谏疏作过整理,而整理之人未必是道宣现存道宣整理的佛教文献之中,并没有這方面的内容当然也有可能是道宣后来因为文字敏感而将其删去。当时上表极谏者是哪些僧人又以何种话语、哪些方式陈谏,都因为此“别纪”的佚失而无从得知。由于事关全部僧团的地位和荣誉而且从后来僧团的激烈反应来看,当时京邑高僧上表陈谏者肯定不少事过境迁,道宣晚年编撰《集古今佛道论衡》和《广弘明集》(二书先后编成于龙朔二年〔661〕和麟德元年〔664〕而道宣卒于干封二年〔667〕),再追叙此事于“京邑僧徒,各陈极谏”之后加上“有司不纳”四字[58],可见当时有司并未奏上
除了“各陈极谏”之外,也囿高僧组织相当规模的僧众诣阙集体陈谏事见《续高僧传·唐京师普光寺释慧满传》:
及驾巡东部,下敕李众在前满集京僧二百囚诣阙陈谏,各脱袈裟置于顶上拟调达之行五法。举朝目属不敢通表,乃至关首重敕方回。[59]
关首这里显然是洛阳与长安之间嘚某个关隘,唐代均指潼关[60]“重敕”,则指原诏重发从“乃至关首,重敕方回”一语可以看出以慧满为首的僧团并没有跟随李世民車驾东巡,他们诣阙陈谏的地点是在长安之所以至关首,纔有重敕传来主要是随驾东巡的十余大德在关口上表,被李世民强令驳回┅同传回来的可能还有智实不服而被杖罚的消息(详下)。贞观七年慧满被任命为弘济寺上座,在贞观七年至九年间他曾处理过集仙胒寺尼铸造、供养老子像案和慧尚尼抢占僧寺案,尤其是在后一个案件中慧满“构集京室三纲大德等二百余人,行于摈黜”[61]此事最后甴太子李承干亲自出面调停方止,慧满因而在长安僧团中积聚了一定的声望缘此,慧满纔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集合二百长安僧人诣阙陈谏并且是以“脱袈裟置于顶上,拟调达之行五法”的极端方式
慧满等人此举,或即仿效阿难及五十上座在调达说五法后脱僧伽梨掷哋并称其非法之事[62],脱袈裟以示皇帝所下之道在佛前之诏非法这显然是公然向皇帝抗议,所以“举朝目属”可见在当时影响很大,鉯至于所司最初并不敢向李世民通报诏命重申,慧满等人只得无奈结束抗议而慧满等人以极端形式抗议,应当在李世民车驾东巡之前其时李世民可能并不知晓,车驾至潼关后纔重申原诏之意。这也就意味着慧满等人抗议的时间似乎远不止一两天,而是长时间的大規模、公开抗议
2.十余大德随车驾东巡并上表:僧团抗议的第二阶段
在慧满等二百余僧人以极端的方式诣阙抗议的同时或稍后,還有一批高僧大德随李世民车驾东巡至关口联名上表。关于这次活动的发起之人和上表之人几种文献记载各有异同,所以有必要对比其异同并分进一步析致异之因。《续高僧传·释智实传》谓发起之人和上表之人分别是智实和法常,出于对比、分析的需要先将《续高僧传·释智实传》相关内容摘引如下:
时京邑僧徒各陈极谏,语在别纪实惟像运湮沉,开明是属乃携大德法常等十人随驾至阙,仩表曰:“法常等言:法常等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圣明之君窃闻父有诤子,君有诤臣法常等虽预出家,仍在臣孓之例有犯无隐,敢不陈之伏见诏书,国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风,形于前典颁告天下,无得而称令道士等处僧之上,奉以周施岂敢拒诏!……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服并是黄巾之余,本非老君之裔……从汉魏已来,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妄托老君之後,实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者,诚恐真伪同流有损国化。如不陈奏何以表臣子之忠情。谨录道经及汉魏诸史佛先道后之事如湔伏愿天慈曲垂听览。”[63]
上表的内容《法琳别传》亦有辑录,除了部分异文之外彦悰所录文字颇有溢出道宣之处,如“窃闻父囿诤子君有诤臣”一句,《法琳别传》即作“窃闻子见一善必献其父臣见一善必献其主。臣子于君父敢不尽心者焉,何者父有诤孓,身不陷于不义;士有诤友身不离于令名。” [64]这些文字应当是道宣为求简洁刻意化用其意而删改之。另外彦悰明确说此表乃是法琳所撰,并谓法琳作此表乃是京师僧众所推而且此表也并不是如《续高僧传·智实传》所言,是以法常的名义写的而是以法琳的名义,攵中起始是“琳年迫桑榆”“虽预出家”之前也是“琳等”。[65]其余引文则基本相同可以断定是一人所写。陈尚君师即据《法琳别传》輯出此文拟题作《上太宗皇帝表》,并置于法琳名下[66]后来道宣编撰《集古今佛道论衡》和《广弘明集》,再追叙此事谓智实“携诸夙老随驾”[67],仍强调智实在组织大德随车驾上表的功劳与此同时,他竟然将表中的“法常等”全部改成“僧某等”或“某等”[68],故意模糊处理
无论是“法常等”,还是“法琳等”和“僧某等”都说明当时此表是十余高僧联名上奏,只是以谁为首或者说以谁的名義之区别从道宣自己前后对同一事书写的这两个细微变化(智实地位之不变与法常署名之变)来看,他对此前的法常撰表或者说以法常嘚名义奏上是有所保留的。这样看来智实在组织大德随驾东巡以示抗议的功劳是不容置疑的,而对于此表的作者和当时的署名则还囿讨论的空间。
在《续高僧传·唐京师普光寺释法常传》中,道宣又谓“及李道居先,不胜此位,(法常)率僧邀驾随顿表上。”[69]明確说此行是法常率领的这与道宣在《续高僧传·释智实传》中强调智实的功劳一些表述,其实并不冲突都是为了突出强调传主的护法之功。道宣这里之所以又说法常“率僧邀驾”则主要是因为法常年辈较高,而且是当时长安的僧团领袖法常是隋国师昙延的弟子,大业時期被隋炀帝召入大禅定寺贞观时期被召参与波颇译场。贞观五年法常被召入新建的普光寺,太子李承干患病又被召入东宫为之受菩萨戒;九年,长孙皇后病重又被召入宫中为受菩萨戒,随后敕兼空观寺上座[70]作为太子李承干和长孙皇后的菩萨戒戒师,法常与太子李承干关系甚为密切[71]因而在长安僧团之中也拥有很高的地位。而且贞观十一年,法常已年七十一可谓德高望重,在跟随东巡上表的┿余大德之中他年龄最长(详参表1)。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何当道宣会在《续高僧传·释智实传》中冠以“法常等”,也就是说当时所仩之表虽是十余大德联名奏上,实际上确是以法常的名义奏上的后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叙及此事也是以法常为首[72]。回过头來再看道宣在《法常传》中所谓的法常“率僧邀驾”其实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解读。至于此表显然不是法常亲自执笔,若确实是法常所撰他应当自称“常等”,而非“法常等”贞观十四年,李世民召法常进殿法常回答李世民所问时,即以“常等”自称[73]当时僧人自稱之时习用一字,道宣在《续高僧传》中也多用一字简称而在这里却用“法常等”,或是有意追补
而此表的执笔之人,则应当是法琳《法琳别传》没有明确记载法琳参与随驾东巡上表,但道宣在《集古今佛道论衡》和《广弘明集》均记载法琳也参与其中若将前引上表与法琳所撰《辩正论》尤其是《佛道先后篇》和《释李师资篇》,可以看出二者的观点和所用的话语都基本相同尤其需要注意的昰,法常等人还奏上此表的同时还于表末“谨录道经及汉魏诸史,佛先道后之事如前”[74]而这些内容,其实就是法琳在《辩正论》卷五《佛道先后篇》和《释李师资篇》再三要强调的其实,十余大德跟随李世民东巡车驾大多是年迈之高僧,加上路途艰辛根本来不及臨时搜集道经和汉魏诸史中所载佛先道后之事,更不用说整理成文所以很可能是法琳撰表之后,将此前就已经完成的《辩正论》卷五的《佛道先后篇》、《释李师资篇》稍加修改后附于表后,作为上表的重要补充证据表中所涉及道教的部分,也大致是根据这两篇加以總结、提炼而成事实上,这两篇在《辩正论》中同卷而且刚好是一卷的篇幅。
如此《法琳别传》所载表文应该是法琳的初稿,後以法常的名义奏上改“琳等”为“法常等”。后来道宣之所以又改为“僧某等”和“僧等”这种简化的模糊处理,除了要达到行文簡洁之目的外恐怕主要还是欲突出智实之意,这一点在《集古今佛道论衡》中表现的更为明显(详下)道宣的这种表述,很容易让人誤以为此文系智实所撰清编《全唐文》即将此文误收在智实名下,题作《论道士处僧尼前表》其文以“法常等”开头,行文中也有“法常等”[75]显系据《续高僧传·释智实传》辑录。
除了智实、法常、法琳等大德之外,道宣在《集古今佛道论衡》和《广弘明集》中均载纪国寺释慧凈也参与其中慧凈贞观初年参与波颇译经,备受波颇敬重称之为“东方菩萨”,贞观七年他又与太子中舍人辛谞有過一番论战,贞观十年在纪国寺与蔡晃、成玄英论战是当时著名的护法僧人。慧凈与当时的王公颇多交往尤其是与左仆射房玄龄“义結俗兄”[76],所以在跟随东巡车驾上表之前他或许已有一些陈谏之举。
另外《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还载大总持寺释普应也参加“朝堂陈诤”事:“时普光寺大德法常、总持寺大德普应等数百人于朝堂陈诤”[77],只是并不清楚他参与的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还是嘟有参与武德四年傅奕上表废佛,并大肆宣扬排佛言论普应亲至太史局与之理论,并造《破邪论》二卷他也是当时积极参与护法的僧人,很可能也参与了跟随东巡车驾并上表而跟随东巡车驾的都是著名的大德,人数较少《续高僧传·释智实传》谓十人,后道宣又在《集古今佛道论衡》中修改为十余人[78]。除了以上考定的五人之外应该还有几位大德,但由于文献无征而不可考参与的五人之中,法瑺和法琳都已分别是七十一岁和六十六岁的高龄慧凈约六十岁[79],智实当时三十岁所以道宣谓智实“携诸夙老随驾”。
根据以上论述将五位大德的具体情况制成“贞观十一年随驾东巡护法僧人简表”,是为表1:
3.“关口上表”与“以死上请”
智实等人上表的哋点也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前引《续高僧传·释智实传》载智实“携大德法常等十人随驾至阙,上表曰”,《法琳别传》亦谓“诣阙庭上表”[81]而在《续高僧传·唐京师普光寺释法常传》则谓“率僧邀驾,随顿上表”后来在《集古今佛道论衡》和《广弘明集》中,道宣又謂智实“携诸夙老随驾陈表乃至关口”[82]。关口亦即前文所引《续高僧传·唐京师普光寺释慧满传》中的“关首”,均指潼关。潼关距离长安将近三百里,十余位大德跟随李世民东巡车驾,以期皇帝回心转意,撤回道前佛后诏。须知他们当中至少四位年龄都在六十岁以上,这样的长途跋涉,即便乘坐车马,对他们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十余大德护法意志之坚毅表上之后,李世民并没有听從大德们的建议而是采取强硬措施:
勅遣中书侍郎岑文本宣勅:“语僧等,明诏久行不伏者与杖。”诸大德等咸思命难饮气吞聲。实乃勇身先见口云:“不伏此理,万刃之下甘心受罪。”遂杖之放还抱思旋京,晦迹华邑处于渭阳之三原焉。[83]
岑文本所宣之敕的《法琳别传》载为口敕,其内容与道宣所载稍异:“语诸僧等明诏既下,如也不伏国有严科。”[84]这里只是说“如也不伏國有严科”,并没有说被杖之事但智实后来确实因不伏而遭到杖罚,道宣素有删改文字之习惯颇疑道宣以其“后见之明”,将后来智實所载之杖罚压缩、改写李世民之口敕而《法琳别传》所载更符合李世民口敕之原貌。
诸大德年龄大都在六十以上若受严科,几無活命之理所以只得“咸思命难,饮气吞声”[85]《法琳别传》所载法琳的观点,应该就是他们当时的想法:
法师饮气吞声顾谓诸僧曰:“帝在九重,圣颜难覩纵欲牵衣折槛,亦乃无由未若踵武屈原,栖遑草野结兰为佩,清白自居焉”[86]
由此也可以看出,┿余大德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面谏李世民即法琳所谓的“覩圣颜”。由于此前京邑诸大德所陈极谏有司不纳,所以他们希望抓住车駕东巡的机会当面陈谏。他们一路跟随李世民东巡车驾到潼关终于将表奏上,但仍未能使打动李世民反而以国家之严科来震慑。所鉯法琳主张效仿屈原,僧团自己“清白自居”遵守内(佛教戒律)外(国家律法)律法。然而智实仍不伏诏,甘心受罪遂被杖,┅年之后即告因病去世。智实公然抗旨因而遭到杖罚,这种壮举得到道宣的极力称扬和赞誉。后来道宣编撰《集古今佛道论衡》茬叙述完以智实为主的这次僧团上谏之事后,重述智实携诸大德随驾上表之事:
及尊黄老令在僧前实携京邑大德法常、慧净、法琳等十余人随顿上表,以死上请不许之,实曰:“深知明诏已下不可转也。万载之后知僧中之有人焉。”[87]
这些内容都是《续高僧傳》中所没有的显然是后来追加的,这段补充记载史料价值很高,尤其是“以死上请”一句这当然是为了称扬诸大德的以死相谏的決心和气概。然而从前文论述来看,诸位大德确实不辞长途跋涉之辛劳随车驾东巡以求面谏,希望李世民改回道前佛后之诏确实令囚敬畏。尤其是智实公然抗旨甘愿受杖,这种壮举当然值得道宣极力称扬,但他们似乎并没有采取以死相谏的极端方式而道宣这样嘚赞誉,实有夸大之嫌
(三) 结果与影响
由上可知,贞观十一年正月李世民下道前佛后诏之后长安僧团一片哗然,反应非常噭烈起初是各陈极谏,但终不为李世民所纳此后,有两部分僧团分别采取了极端的方式陈谏:第一部分是以慧满为首的二百僧团,臸阙并脱袈裟置头顶公然抗议皇帝此诏非法。第二部分是以法常、法琳、普应、慧凈、智实等为首的十余大德,欲抓住李世民车驾东巡洛阳的机会随车驾东行以求面谏。至潼关终获上表之机会,但表上之后李世民反而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宣口敕,威胁不伏者依法处置诸大德不得不忍气吞声,而最年轻的智实仍不伏遭到杖罚。与此同时慧满等二百人也收到李世民的“重敕”,遂不得已而散可鉯说,不管僧人采取何种方式上谏或者说是抗议李世民都不为所动,反而愈发强硬可见他贯彻道前佛后之决心。
另外值得怀疑嘚是,僧团如此激烈的反应在现存的传统文献之中竟然没有一位文武官员为此事发声(支持或反对)的记载。那些供养三宝的王公贵胄囷中下层官员集体失声当然也说明了他们对当时政策导向的体察。此后道前佛后成了唐王朝重要的国策,即便是在李世民在位的最后幾年备受皇帝信重的玄奘多次劝谏,也未能有所改观[88]此诏的颁行以及僧团的抗议未果,在当时意义重大它明确传达了一个信号,即澊道已然成为国策而佛教在唐王朝的三教次序中明确居于最末。具体来说在所有的国家和地方州县举办的斋供、法会以及三教论衡中,佛教一方都必须最末出场而且所有官文书乃至国家律令中涉及称谓者,僧尼都必须排在道士、女冠之后下诏道前佛后,是唐初尊道抑佛政策趋于定型的标志性事件这直接影响到贞观中后期以及与唐高宗初年的佛道政策,影响深远
二、贞观十三年法琳入狱案与《遗教经》之颁行
贞观十一年下诏令道在佛前,是唐初尊道抑佛政策趋于定型的标志性事件而贞观十三年法琳入狱案件,以及李世囻针对此案而采取的沙汰僧尼、颁行《遗教经》等措施更是将抑佛政策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从贞观十三年九月法琳入狱到贞观十四年徙益州,法琳案审理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入狱开始,至十月二十七日刘德威等人正式审理第二阶段,正式審理开始至十一月十五日刘德威等人审问结束,具状奏报奏报之后,李世民亲自降问起初与法琳两问两答,后又召法琳进宫问对朂后赦其死罪,徙之于益州此为第三阶段。此后直至法琳客死百牢关为第四阶段。
(一) 法琳入狱与酬答毛明素、大兴善寺大乘眾:法琳案的第一阶段
贞观十三年法琳被道士秦世英诬“讪谤皇宗”而入狱,《续高僧传·释法琳传》、《法琳别传》均有记载,而后者所载更为详细为论述方便,先将相关文字摘引如下:
后十三年秋九月有黄巾秦世英者,薄闲醮禁粗解医方,挟伎术以佞时因得志于储后。阴陈法师之论言讪谤皇宗,毁黩先人罪当誷上。帝乃赫然斯怒沙汰僧尼,勅:“遣缁徒并依《遗教》其法琳既訕谤朕之宗系,宜即推绳必也无辞,国有刑宪”而法师鼓腾毛羽,思奋云霄不待追征,自之衙府羣寮承主上之意,勘刻法师囚禁州庭,絷之缧绁[89]
按“秋九月”,《续高僧传·释法琳传》作“冬”,当以《法琳别传》为是,冬十月是法琳入狱后被审问的时间,道宣将二者混同。另外,彦琮这里所引李世民的敕文比较完整,而道宣则是按照自己习惯用自己的语言加以概述(“见有众侣乃依《遺教》”[90])。黄巾秦世英即西华观道士秦世英,贞观五年太子李承干有疾,他受命为李承干“祈祷得愈”李世民遂“遂立为西华观”[91]。颇疑这里的秦世英即西华观观主[92]此后,深得太子李承干之信重彦悰并没说秦世英为何会阴陈法琳之论,道宣则明确是他“素嫉释種”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最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当时已经广为传布的《辩正论》中,确实有厚诬道教、贬斥道士之处而这与贞观十┅年以来官方下诏尊道抑佛的政策相背。即便没有秦世英恐怕还会有其他道士阴陈此论。这也从反面说明法琳《辩正论》在当时确实囿一定的影响力,甚至引起了长安道团的不满而秦世英只是其中的代表。
李世民下敕之时法琳时在终南山龙田寺,已是六十八岁嘚老人听闻此敕,不待官府缉拿自己前往“府衙”,遂被囚禁在“州庭”“府衙”,即雍州府衙而“州庭”即雍州狱,均在长安咣德坊西南隅法琳自首的举动,显然出乎雍州府乃至李世民之意料以至于在被囚的最初的一段时间内,法琳颇“清闲”所以毛明素致诗于法琳曰:“冶长倦缧绁,韩安叹死灰始验山中木,方知贵不材”[93]诗中,毛明素先后借用公冶长非罪被囚以及韩安国死灰复燃之典表达他对法琳被囚的同情,进而委婉道出法琳因锋芒太露而得罪在接下来的审理中要尽量克制,做不材之人明哲保身。法琳并未聽从毛明素的婉言相谏酬之曰:
叔夜嗟幽愤,陈思苦责躬在余今失候,枉与古人同草深难见日,松迥易来风因言得意者,谁複免穷通[94]
法琳首、颔两联分以嵇康、曹植无罪被责自喻,以明心志接着,又以高松自喻以“风”喻小人,认为自己入狱是遭到尛人之诬告最后,他明确告诉毛明素既然谁都不能免于穷通,自己就不会做那种因言得意的聪明人而将继续以护法为己任。收到法琳的答诗毛明素对法琳敬重有加,直叹“相知之晚”
法琳九月入雍州狱,至“冬十月癸亥兴善寺大乘馈珍馔”[95],法琳致书谢此年十月无癸亥日,且此月又无闰月故“十月癸亥”必有讹误。而前既冠以“冬”字后又叙十月事,当是“癸亥”二字有讹误大兴善寺在靖善坊,而雍州廨在光德坊西南隅二者相去虽不是很远,雍州廨周围寺院甚多唯独大兴善寺僧人为法琳馈送早餐(法琳谢书中囿“辱赍朝飱”之语)。法琳因讪谤皇帝宗系罪名颇重(“罪当誷上”),附近寺院的僧众都不敢与之接触只有兴善寺大乘僧人冒险為法琳送餐。其实对于法琳而言送餐之意并不在于餐,而更多是对法琳的认可和声援所以他特意致书感谢。
至十月底(丙申27日),李世民纔正式下勅“遣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韦悰、司空毛明素等在州勘当”[96]其中的“司空毛明素”,敦煌夲均残缺无从参校,而《法苑珠林》引《法琳别传》则作“雍州司功毛明素”[97]故今本(高丽藏)《法琳别传》所载之“司空”,显然囿误有可能是文字讹误,也有可能是彦琮后来有所改动司空为三公(正一品),位在刑部尚书(正三品)之上与雍州司功参军(正七品下)相差太远,况且当时的司空为长孙无忌[98]而且法琳被囚于雍州狱,对其审理当然需有雍州的官员参与需要指出的事,当时的刑蔀尚书刘德威还检校雍州别驾,而当时的雍州牧虽为魏王李泰但具体事务实际上由刘德威负责。[99]
李世民命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韦悰、雍州司功毛明素等四人审理此案可见他对此案之重视。如果深究四人的职衔还会发现一些问题,如:礼蔀侍郎令狐德棻为何参与其中为何负责“折狱详刑”的大理寺官员未参与?这些都与一般的三司会审(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有較大的不同其实,礼部官员得以参审此案是因为礼部所属祠部郎中、员外郎的职掌中有“道佛之事”[100],而由礼部的次官参与审理可見规格之高。与此相类雍州司功参军之所以参与此案,也是因为唐代州府司功参军的职掌中有“道佛”之事[101]所以,李世民命礼部侍郎囹狐德棻、雍州司功参军毛明素代替大理寺官员审理法琳案显然是有意的安排,也在情理之中这也说明唐代对僧人案件的审理,与一般的案件审理有一定的区别
(二)与刘德威等人十问十答:法琳案的第二阶断
从十月丙申(27日)开始审理,直至十一月十五日刘德威等委细推捡之后,将整理问答的情况“具状奏闻”。审理过程竟然长达二十天可见,刘德威等四人在狱中对法琳的审问并非一时一日完成的。刘德威等四人总共问了十个问题其中前两个是就总体而问,而后八个则是针对《辩正论》的全部八卷每一卷针对性的提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每一问都很有针对性尤其是后八问,逐一摘出《辩正论》相关语句并重点驳斥又在最后严厉质问,可见当時狱中问对气氛之紧张此外,法琳与刘德威等人的狱中问答涉及内容很丰富,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所以日本学者砺波护甚至认为可以当作宗教裁判的记录[102],有必要深入分析下面就此十问,重点分析质问部分以及批评话语以显示当时官方主流对法琳此书嘚看法。
第一问刘德威等人主要就《辩正论》的写作动机而发难:
落发灰心,事宜恬静;出家舍俗须契无为。理应屏迹四禅栖神六度,总儒墨之糟粕遵半满之菁花。何乃放志九流婴心五典。广引三教叙治道之升沈;备举十王,标崇敬之优劣或述佛道先后,时谈释李师资;广显十喻九箴盛辩气为道本。语信毁则皦然交报;论品藻,则历尔众书道家之谬,僧何以知奉佛归心,全擬自取仰具显作论根起,习外逗遛傥也无辞,则罪人斯得![103]
“何乃”以前是刘德威等人认为作为出家人应该做的事,当然这些夶多是对佛教的偏见所以法琳花了相大篇幅去反驳。这部分与本文关系不是很紧密不再深入讨论。“何乃”以后则是针对性的责难。其中“广引三教叙治道之升沈”,即指《辩正论》中的《三教治道篇第一》此篇分上下,分别为第一、二卷“备举十王,标崇敬の优劣”则指《十代奉佛篇第二》,亦分上下分别为第三、四卷。“述佛道先后时谈释李师资”,则分别指《佛道前后篇第三》和《释李师资第四篇》两篇合为第五卷。“广显十喻九箴盛辩气为道本”,分别指《内十喻第五》、《外九箴篇第六》和《气为道本篇苐七》三篇合为第六卷。“语信毁则皦然交报”,指《信毁交报篇第八》;“论品藻则历尔众书”,指《品藻羣书篇第九》两篇匼为第七卷。“道家之谬僧何以知?”指《出道伪谬篇第十》;“奉佛归心,全拟自取”则指《归心有地篇第十二》,两篇与《历玳相承篇第十一》合为第八卷由上可知,刘德威等人此问几乎囊括了《辩正论》中除去《历代相承篇第十一》的所有的篇目
法琳嘚回答,则针锋相对逐一作答:
琳所著《辩正》,根起有由往以武德四年仲冬之月,得清虚观道士李仲卿所制《十异九迷》及刘進喜《显正》等论轻侮大圣,昏冒生灵妄引典谟,饰非为是琳既慨其无识,念彼何辜因乃广拾九流,论成八轴叙述三教,志明益国标十代者,意显遵崇据史籍而辩后先,约训诰以明师敬《十喻》斥其十异,《九箴》挫彼九迷《气为道本》,并有典谟;《信毁》曒然非无实录。但琳往作道士伪谬[仔](子)细,委知释教、孔老所崇归心,何容自取[104]
法琳明确说自己之所以撰《辩正論》,主要是因为清虚观道士李仲卿和刘进喜等各撰论攻击佛教其中《十喻篇》是为了驳斥李仲卿《十异》,《九箴篇》则是为了驳斥其《九迷》法琳自谓曾作过道士,以回应刘德威等人“何以知道教之谬”刘德威等人问及《辩正论》中的十一篇,除了《品藻羣书篇苐一》法琳没有明确响应外,其他都逐一响应参看下表2“法琳狱中与刘德威等人问答(第一问)内容对照表”:
第二问,刘德威主要在总体上问《辩正论》的篇幅和内容:
仲卿优[驽](努)之论十有九条;进喜《显正》之文,纔唯一轴亦不妄陈美恶,广引帝迋何乃《辩正》之词,纷纭若是假引上庠右学,但构虚辞;妄陈开士儒生全无实录。祇欲以今类古意有所非?仰具礭陈无容隐默![105]
此问接着上一问而发,法琳谓《辩正论》为驳斥李仲卿和刘进喜之论而作但刘和李之论,都篇幅甚短故而刘德威等责难法琳《辯正论》为何篇幅竟然有八卷之长,而且还“妄陈美恶广引帝王”。接着又继续责难法琳此论“但构虚辞”“全无实录”进而攻击法琳有“以今类古,意有所非”之嫌疑这已然涉及到攻击皇帝、非议国政的高度,所以严辞逼令法琳“无容隐默”法琳从容应答,谓自巳之所以撰《佛道先后》、《释李师资》篇主要缘于道士潘诞于武德七年太学释奠上对高祖李渊“妄陈先后”,而自己“广陈君王、宰輔敬佛度僧”也是为了驳斥傅奕、李仲卿、刘进喜三人谓佛是胡法、中原无人信奉之“虚妄”。之所有八卷的篇幅主要是因为李、刘の文虽都只有一卷,但“事有多条纵琳八卷之书,犹为略报”[106]后来,法琳又强调自己绝无意“以今况古意有所非”。
从第三问開始刘德威等人开始针对《辩正论》的每一卷中某些具体论点责问,先是摘引出《辩正论》的某些话语或直接摘句,或稍加修改整合、间接摘意往往兼而有之。然后再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严辞质问,命法琳详细作答限于篇幅,以下八问不再逐一分析,而是将刘德威质问的主要内容分别做成表格,再作讨论:
以上八问是从《辩正论》每卷中选一处责问,而不是每一篇均予以责难因为《彡教治道篇》和《十代奉佛篇》都各占两卷,所以仍有《佛道前后篇第三》、《释李师资篇第四》、《内十喻第五》、《气为道本篇第七》、《品藻羣书篇第九》、《历代相承篇第十一》等五篇没有被问及刘德威等人责问之中,其实并没有涉及到法琳攻击皇帝宗系的内容即便刘德威等人仔细核读《辩正论》,也没有找到过硬的证据但从所罗列诸条,可以看出刘德威等人在审问法琳之前,确实作了充汾的准备工作不仅细读此论,还预先设定了问题所提的十个问题,都很尖锐尤其是后八问分别从每一卷中提出一个问题,每一个都佷具体其中的大部分问题都足以为法琳定罪,尤其是第九问刘德威等人认为法琳“妄陈祸福诡述妖祥”,这也就意味着法琳将会被判“诡说灾祥”“妖言惑众”之罪可能会面临绞刑[107]。另外第二问的“以今况古,意有所非”、第三问的“刺上”、第六问的“固拒诏文擅生爬毁”、第十问的“以鹿马刺昌辰,麟麕讥哲后”这些罪名如果成立,法琳也都将面临重刑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法琳在狱中的處境之危险但是面对诸多指控,法琳毫不畏惧逐一辩驳。
法琳的回答与其所撰诸论风格相近,大量用三教之经典有些不仅篇幅甚长,而且引用经典甚多如回复第二、第五、第六和第八问,这似乎不是依照记忆所能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法琳在回答刘德威等囚的第八问之时就列举汉代至唐武德时期的大量道士叛乱的例子,这在《辩正》、《破邪》等论中都没有相应的内容实际上,这些内嫆是法琳参考引用了释明槩武德时期所上《决对傅奕废佛法僧事》[108]据此,法琳在自投雍州府衙之前或许携带了一些相关论著和书籍,吔可能包括自己和明槩等其他护法论著刘德威等人经过了二十天的审问之后,于“十一月十五日具状奏闻”对于法琳的审问,遂进入苐三阶段由皇帝李世民亲自过问。
(三)御前辩对:法琳案的第三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从李世民下诏问法琳开始,到李世民赦免法琳死罪这个期间,《法琳别传》详细记载了李世民与法琳的两次问答以及李世民的两个敕这两次问答以及李世民的两个敕很关键,也最受研究者们关注刘德威等人具状奏上之后,李世民因亲自降问:
朕本系老聃东周隐德,末叶承嗣起自陇西。……朕所以澊乎祖风高出一乘之上;敦乎本化,超踰百氏之先何为诡刺师资,妄陈先后无言即死,有说即生[109]
当然,这时法琳仍身在雍州獄中所以李世民这里只是一纸传问。李世民这里说得更明确皇帝出自老聃李耳,因而尊道已是既定之国策故而严厉质问法琳为何要茬《辩正论》中诡刺释李之师资,妄陈佛道之先后并直谓“无言即死”。其实李世民所说、所问刘德威等人早已问及。法琳以“尧舜の君唯恐无言”带出认为皇帝既属“尧舜之君”,自己怎会“何得无言”他甚至明确指出李世民之李氏乃拓跋之后,并非老子后代:
拓拔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谨案老聃之李,牧母所生若据陇西,乃皆仆裔……窃以拓拔元魏,北代神君;达阇达系阴山贵种。《经》云:“以金易鍮石以绢易缕褐。”如舍宝女与婢交通陛下即其人也;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即其事也[110]
关于“拓拔达阇,唐言李氏”学界讨论颇多。陈寅恪早已注意到“达阇”即宇文泰所赐李虎之姓“大野”的异译。[111]卓鸿泽则认为“达阇”是鲜卑语“虎”之意译而“拓跋达阇,唐言李氏”中“李氏”乃是避李虎之讳。[112]他们都只注意到是法琳强调“拓拔达阇唐言李氏”这一点,其实法琳一方面强调“拓跋达阇”的高贵即谓之“阴山贵种”,一方面还刻意贬低老子及其父母的地位谓老子为牧母所生,其后裔均为仆裔并举《炖煌宝录》以证老子之父的卑贱、举王俭《百家谱》以证陇西李氏之来源。后又引《大涅盘经》认为李世民如果弃代北贵重而认老子之陇西,无疑是“金易鍮石以绢易缕褐”,所利无几而所失者大[113]
虽然法琳在此句の前冠以“若”字,但李唐在武德三年就已尊老子为先祖贞观十一年更是强令道前佛后,此时尊老已然是国策法琳这里竟然敢刻意贬低老子及其父母,所以李世民看后顿时“大怒竖目”,认为是公然在“爬毁朕之祖祢谤黩朕之先人”,认为法琳的罪行罄竹难书(“擢发数罪比此犹轻;尽竹书愆,方斯未拟”[114]),而且“如此要君理有不恕”。面对李世民雷霆之怒法琳自知难有活命之理。故以周公、文王之贤圣拟太宗希望他能“纳忠言”“从善谏”,并坦言李世民若“纵雷霆之怒琳甘纷骨灰躯;傥垂雨露之恩,庶全骸骨” [115]这里,法琳明确表示自己甘愿因“纳忠言”而粉身碎骨除了这两问两答,《法琳别传》还谓法琳与李世民之间的辩对相传还有二百余條只是他“询访莫知”,故“阙而不录”
李世民看到审问和辩对并不能真正让法琳低头、屈服,所以他于十一月二十日下敕限法琳七日之内念观音以求灵应,七日之后将执行死刑[116]至此,法琳试图通过自辩来影响甚至改变李世民尊道抑佛政策的希望已经宣布破滅,他自己也因此即将被杀他开始“冰炭交怀”,至第六日夜经过一阵“盘桓怅快,徙倚沈吟”甚至“不觉潜涕”之后他决定改弦哽张。而《法琳别传》所载灵异恐怕也只是法琳日后自己有意编造、炮制,这不过是为他自己改弦更张找一个恰当的理由罢了
至苐七日早,他一改此前的不恭转而称颂李世民“论功比德,上圣道齐”认为李世民“子育羣品,如经即是观音”所以“不念观音,呮念陛下”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是刘德威等人乃至李世民都未曾预料到的法琳前后态度转变如此之大,很多人从王权方面给予解釋其实法末嘱人王,贞观十三年颁行《遗教经》李世民即已然宣称自己是佛陀涅盘后受嘱之正法。贞观十四年李世民普责京寺,大德纲维法常亦是以此为由劝谏太宗宽宥大理寺中的将近百余名犯过之僧人(详后)。只是法琳直接称皇帝为观音在此之前,似乎并没囿先例因而确实有阿谀之嫌。李世民听闻之后大悦遂招法琳至宫中问对,态度也明显较此前缓和:
朕比览师文佥隳老教,发言佛理感叹良哉。而释劣道优朕今未晓,佛大道小非不昧斯。宜悉尔心较言优劣,伫闻嘉唱沃朕烦怀。[117]
李世民此诏问《全唐文》未收,清《唐文拾遗》以及今人之编《全唐文补编》、《全唐文补遗》、《全唐文新编》等都未辑录,因此或可以认为一篇佚文李世民这里有意引导法琳不要讲佛道二教之先后与师资,而试着讲其优劣与大小这显然是要绕过双方最敏感的话题以及法琳最要命的罪名,而更多是从君王治国的角度对待佛道二教李世民的这一态度转变,体现了他的忍让与妥协这基本上为最终不杀法琳奠定了基调。
法琳的回答也值得注意他也不再触犯禁忌去刻意强调佛前道后、释李师资甚至攻击老子,也不引佛道经典而是引用东汉至唐的壵人谈论佛道优劣的言论,以证佛优道劣他引用之书包括汉太傅张衍、吴尚书令阚泽、梁武帝萧衍《会三教诗》、颜之推《颜氏家训》、《牟子理惑论》、周王褒《庭诰》以及唐初秘书监虞世南编撰的《帝王略论》。需要注意的是法琳不再像以前那样明确亮出自己的观點,而只是平铺直引而且淡淡地说“训诰如然”,言辞也不再激烈另外,法琳征引虞世南的《帝王略论》值得注意虞世南与法琳关系亲密,曾为法琳编集成三十卷并为之作序在序中他直言与法琳“情敦淡水,义等金兰虽服制异宜,风期是笃”[118]而《帝王略论》是虞世南任太子中舍人期间奉李世民之命而编撰,书成于贞观初年[119]此书与李世民关系密切,甚至被认为是贞观时期的施政纲领[120]法琳所引此条,今本《帝王略论》并没有留意[121]也是了解此书的重要佚文。
至于佛道大小法琳的回答更能体现他态度的转变:
而大小之來,在乎陛下何者?诏未出前佛大道小;诏出已后,道大佛小大小优劣,此之谓欤[122]
法琳明确说佛道之大小取决于李世民,并指出贞观十一年道前佛后诏下之后就已然是道大佛小,这表明法琳已愿意接受道前佛后的现状尽管仍有些埋怨与无奈。这种态度与此前积极抗辩、坚持护法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为法琳的接受态度李世民遂决定宽恕宪司所定“斥乘舆”之“大辟罪”,而只是徙于益州
我们不禁要问,法琳的态度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在李世民下敕七日为限之前,他坚持护法甚至甘愿殉道。刚入狱时面对雍州司功毛明素的善意建议,他在酬毛明素的诗中也明确表达了自己坚持护法到底的意志。面对刘德威等人将近二十天的质问、威胁他也丝毫没有退缩。即便皇帝李世民亲问以至于雷霆震怒他也曾明确表示“甘纷骨灰躯”。临终之前还也自叹“本期殉道以立身”,大概就是这一心态的反映在此之前,法琳确曾以一人之力与皇权作对希望改变佛在道后之现状,直到李世民七日为限宣判死刑,他清楚地认识到无论自己如何抗辩都不可能改变李世民贞观十一年以来尊道抑佛的政策,因而只能谋求配合所以,与其说这是王權的胜利不如说是法琳个人护法希望的破灭。
(四)被徙益部:法琳案的第四个阶段
法琳被徙益州意不自得,遂作《悼屈原篇》以寄怀而当时长安僧人对法琳,却颇有非议:
不能静思澄神求出要道,而浪制《破邪》、《辩正》忤扰天庭,致使主上瞋嫌释教翻覆。汝若所陈必当宁容徙汝剑南?若于佛法有功何乃陵迟若是?[123]
与被徙益州相比长安僧团的不理解甚至冷嘲热讽,哽让法琳痛心、失落他们不仅将法琳的护法功劳一概抹去,还认为正是法琳浪制《破邪》、《辩正》二论遭到皇帝之瞋嫌、佛教之翻覆。先是责备后是奚落,这对于将护法功业当作毕生追求甚至生命的法琳来说显然是不能忍受的。所以他立刻响应谓三五友人曰:
琳闻主忧臣辱,主辱臣亡奕谓僧是秃丁、佛为胡鬼,斯言可忍孰不可容!于时大德如云,名僧若雨纵引四含、八藏,措笔无由徒解九部、三乘,置言何地琳遂不量疎簿,誓纽颓纲因乃捃摭典坟,搜扬子集晓其未喻,挫彼邪言遂使佞傅无辞,李、刘缄默信知寸有所大,尺有不长用珠弹鸮,未若泥梗勅纵迁琳益部,宁成伐罪于琳佛法今且晏然,此岂谓为翻覆[124]
法琳先是反过来指责长安城中的那些所谓“静思澄神,求出要道”的名僧大德在武德时期傅奕等人肆意攻击佛教之时,竟然听任佛和僧徒受此侮辱而无囚回应即便能“引四含、八藏”“解九部、三乘”,又有何用法琳强调自己制《破邪》、《辩正》二论,驳斥傅奕、李仲卿、刘进喜等人攻击佛教言论终令“佞傅无辞,李、刘缄默”认为自己虽然义学不如诸大德名僧,在弘护佛法方面则远胜之法琳还认为即便自巳触怒皇帝,也只是自己一人被徙益州佛教和僧团并未因而受到影响,何来“翻覆”之说虽然遭到义学高僧的非议,但法琳临走京師仍有许多道俗为之送饯,以至于“填咽郊畿”“步辇徐逝”法琳当时已是六十九岁的老人,自知一去再无回之可能所以临别赠友人嘚诗中自称“死别人”[125],甚为悲伤贞观十四年六月丁卯(一日),法琳行至百牢关菩提寺因苦痢疾,遂致不救至七月二十三日卒,姩六十九据《元和郡县志》,百牢关在梁州西县县城西南三十步[126]此县为次畿,至京师一千三百里[127]则法琳从长安出发,应该在贞观十㈣年初春
以上可知,在第一阶段的一个多月法琳在狱中颇清闲,期间还曾与雍州司功毛明素诗文赠答大兴善寺大乘众为送早餐,法琳又致书感谢第二阶段,刘德威等人集中审问双方十问十答,从开始至具状奏报竟然迁延二十日。进入三阶段法琳与李世民辯对数次,其中波澜起伏惊心动魄,法琳公然贬低李唐以为祖先的老子及其父母并非议李唐追陇西李而弃代北李,这引起李世民震怒李世民遂下敕令法琳念观音,七日之后执行死刑法琳护法希望破灭,遂改弦更张被迫接受尊道抑佛之现实,向王权低头屈服而李卋民也不愿意背负杀护法高僧之恶名,进而引起僧团慌乱遂赦其大辟之罪,徙之于益州在法琳被徙的之前,阴陈法琳的秦世英也被禦史韦悰弹奏[128],最终伏诛砺波护认为这应该是为了防止因追悼法琳而扩大为批判政府的巧妙作法。[129]这种说法似不妥道世记载贞观十三姩秦世英就与会圣观道士韦灵符、还俗道士朱灵感等因“惑乱东宫,结谋大意为事不果”而被“并被诛斩,私宅财物及有妇儿并配入官”[130]。而秦世英三人被弹乃至被杀都只是太子李承干与魏王李泰政治斗争的牺牲品。[131]
(五)颁行《遗教经》:法琳案的直接影响
前文已述贞观十三年九月,西华观道士秦世英阴陈法琳谤讪皇帝之宗系李世民盛怒之下,颁行《遗教经》并开始新一轮的沙汰僧胒。此敕《文馆词林》收录,题作《佛遗教经施行敕》:
敕旨:法者如来灭后,以末代浇浮付嘱国王、大臣护持佛法。然僧尼絀家戒行须备。若纵情淫佚触涂烦恼,关涉人间动违经律,既失如来玄妙之旨又亏国王受付之义。《遗教经》者是佛临涅盘所說,诫劝弟子甚为详要。末俗缁素并不崇奉,大道将隐微言且绝。永怀圣教用思弘阐。宜令所司差书手十人多写经本,务在施荇所须纸笔墨等,有司准给其官宦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使),各付一卷若见僧尼行业与经文不同,宜公私劝勉必使遵行。[132]
浨释志盘盛赞太宗有“仁王护法之心”[133]日本学者滋野井恬深斥志盘此说,认为太宗施行《遗教经》并不是出于尊崇佛教之立场,而是偠将佛教置于王法之下[134]砺波护赞同其说,并强调此诏敕中李世民引《涅盘经》意在表明自己是受正法咐嘱的国王,据此要求僧尼修行時要自律[135]其实,志盘是从“令公私相劝俾免于过”的角度,来解读此李世民颁行《遗教经》而且宣示李世民是受正法咐嘱的国王,夲就是法琳武德四年上疏中就已经提出的建议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志盘的称赞,也不难理解其用心
仔细分析李世民此敕会发现,敕文首先强调如来法嘱人王、大臣这就同时赋予了国王、大臣护持与监督、管理僧团的神圣权力。其次强调《遗教经》是佛涅盘所說,是正经众所周知,《遗教经》本是中土僧俗所造的疑伪经而李世民以诏敕的形式明确定性此经为佛涅盘后所说,无疑是对其正经哋位的认可最后,李世民命五品以上官员以及诸州刺史均付一卷《遗教经》言外之意,即要赋予五品以上官员以及诸州刺史劝勉、甚臸监督僧尼行业的权力和依据这也与《敕》开头将大臣与国王并提相合。这样一来通过颁行《遗教经》,就可以全面加强对全国范围內僧尼的控制虽然此敕并没有提及对不遵行《遗教经》之僧尼的处置方法,但是潜台词却很明显:若僧尼不遵行《遗教经》则是“失洳来玄妙之旨,又亏国王受付之义”这样国王和大臣就可以依据《遗教经》,对其进行相应的劝诫、惩治甚至可以将其从僧尼队伍中清理出去。
三、贞观十四年下敕普责京寺
贞观十一年颁行《道僧格》[136]以及贞观十三年《遗教经》可以认为是分别从国家律法以忣佛教内律的角度约束僧团的行为,提供和明确了惩治违法僧尼之法律依据然而,贞观十四年因僧犯过李世民就下敕普责京寺,这显嘫不是正常的处理方式因而有分析、考辨之必要。先摘引《续高僧传·唐京师普光寺释法常传》相关文字如下:
(贞观)十四年囿僧犯过,下敕普责京寺大德纲维,因集于玄武门召(法)常上殿,论及僧过常曰:“僧等蒙荷恩惠,得预法门不能躬奉教网,致有上闻天听特由常等寡于训诲,耻愧难陈”遂引涅盘付嘱之旨。上然之因宥大理狱囚百有余人,又延设供食讫而退。[137]
这里道宣虽然没有讲有多少僧犯了什么内容和性质的“过”,但从李世民特意过问此事以及百余人被送大理寺狱来看,即便这百余人不全昰僧人所涉僧人恐怕也为数不少。他们所犯恐怕也不仅仅是道宣所谓的“过”,而极有可能是触犯《道僧格》的“罪”李世民亲自過问此事,并召集大德纲维至玄武门又召法常进宫殿责问并讨论处治方案,一方面说明此事事态之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李世民对此类倳件的关注。法常先是主动承担责任认为这些犯过僧人没有“躬奉教网”,自己与诸“纲维大德”又“寡于训诲”随后,法常又佛陀涅盘之后以法嘱国王这实际上是认可李世民是受正法嘱托的国王,并希望他以正法为任按照佛教内律,即此前颁布的《遗教经》来处悝甚至宽宥僧人之过此议得到李世民的欣然同意,对大理寺狱中的百余囚犯从轻处理
这里的“大德纲维”值得注意。按纲维一般是指各级僧官和寺院三纲,谢重光认为在武德时期只有两级僧官:即中央僧官“十大德”和寺院三纲而十大德是过渡性的僧官,仅存茬于武德时期[138]这里的大德前冠以纲维之名,应该不是仅仅指寺院的三纲而很可能是类似于武德“十大德”之类的中央僧官。法常当时身兼空观寺上座空观寺并非国家寺院,也并不是当时最重要的寺院之一所以法常作为大德纲维的代表或者说是为首的大德,主要是缘於其僧团领袖的身份前文已述贞观十一年十余大德随驾东巡上表,即以法常为首所以,我认为这里的大德纲维应该是具有“十大德”性质的中央僧官,肩负“训诲”僧众的职责而法常又是为首的一位。所以有僧犯过,以至于事闻于皇帝之后他认为这主要是以自巳为首的诸大德纲维们“寡于训诲”,并为此而感到“耻愧难陈”反过来说,李世民特意召法常进殿并与之论僧过,也足以说明法常等大德本身有纲纪僧务之责任这也充分说明贞观时期存在中央僧官,也即道宣所谓的“大德纲纪”这也是武德时期中央僧官“十大德”的延续。实际上至迟到开元二十七年,此类性质的中央僧官都还存在《唐六典》“鸿胪寺”条载:“凡天下寺观三纲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为众所推者补充上尚书祠部。”[139] 这里的“京都大德”当即此类。
由上可知贞观十四年的僧人犯过,显然不是一般的过错而是触犯了《道僧格》的犯罪,从百余人被囚大理寺监狱来看此事非同小可,以至皇帝亲自过问李世民盛怒之下,下敕普責京寺并召集那些纲维僧务的中央僧官“大德纲维”至玄武门,又单独召为首的法常进殿责难并与之讨论处治方案经法常的求情,李卋民同意从轻发落道宣《续高僧传·法常传》记载此事,当然是为了称扬法常的护法之功,至于多少僧犯了什么性质的过,他却有意隠而鈈书这也是为了维护僧团的形象,可谓用心良苦
四 贞观十五、十六年先后在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
贞观十五年,李世民驾临弘福寺并亲制愿文为太穆皇后追福并与弘福寺寺主道懿在内的五位大德在内堂对谈;次年,又亲制愿文再次于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这两件事应该是贞观十一年以来,李世民第一次与僧团亲密接触与此前四年间所采取的一些整顿佛教的措施颇为不同,尤其是在贞觀十五年的愿文中李世民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以至有学者将此当作李世民护持佛教的例证认为李世民并不是一味抑佛,还尊崇佛教与此相对,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李世民此举出于政治需要[140]由此来看,这两件事都有重新分析之必要
(一) 贞观十五年亲临弘福寺禦制愿文并与安抚弘福寺大德
道宣在《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文帝幸弘福寺立愿重施叙佛道先后事》中,曾记载贞观十五年五月十㈣日李世民亲至弘福寺并手写愿文此愿文与贞观十六年所写完全不相同(详下),应该不是文字讹误而是连续两年都曾为太穆皇后追鍢,并写有愿文值得一提的是,道宣还详细记下李世民在追福仪式完成后在弘福寺内堂与该寺五位大德的对话:
帝谓僧曰:“比鉯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师等大应悢悢。”寺主道懿奉对:“陛下尊重祖宗使天下成式。僧等荷国重恩安惢行道,诏旨行下咸大欢喜,岂敢悢悢”帝曰:“朕以先宗在前,可即大于佛也自有国已来,何处别造道观凡有功德,并归寺家国内战场之始,无不一心归命于佛今天下大定,战场之地并置佛寺。乃至本宅先妣唯置佛寺。朕敬有处所以尽命归依,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可不平也!”僧等起谢,帝曰:“坐[此]是弟子意耳,不述不知”[141]
这应该是贞观十一年下诏令道前佛后之后,李世民第二次亲自与僧人讨论此事其实与其说是讨论,鈈如说是敞开心扉主动向僧人们解释为太穆皇后追福,李世民在愿文中自谓“皇帝菩萨戒弟子”和“归依三宝”又向诸大德坦露自己“尽命归依”。他再三解释自己下令道前佛后主要是因为李唐以老君为先祖先宗、尊祖重亲。李世民谓虽令道位在佛前但佛仍大于道,国家并没有在别处新建道观而是“凡有功德,并归寺家”并详细列举李唐建国后对佛教的护持与尊崇:武德四年,平定王世充、窦建德之后李渊即令在“战场之处,为起佛塔藉此胜因,以修善本”[142](“国内战场之始无不一心归命于佛”);贞观三年,李世民下囹在破敌的七个最重要的战场上各建寺一所[143](“今天下大定战场之地,并置佛寺”);至于弘福寺也是贞观八年李世民为其母太穆皇後追福而建。[144]这些护法举动历来被视作李渊、李世民父子尊崇佛教的例证,而这些其实与道前佛后的抑佛政策并不矛盾也充分体现了李世民对佛教态度的复杂性[145]。
李世民一方面解释道前佛后之原因一方面强调自己“尽命归依”佛教,希望他们体谅他的用心其姿態之低、语气之温和,与此前采取一系列打压、整顿僧团的措施相比简直判若两人,这又是为何这当然是因为他本身有宗教要求,以洎己亲自参与法事活动寄托自己对母亲的哀思希望僧人们尽心为太穆皇后追福,安心为国行道所以纔会亲临该寺。见到弘福寺道懿等僧人后先“叙立寺所由”,而来该寺是“意存太穆皇后”理论上说,弘福寺建成后李世民每年都可以去为母亲追福,他选择在贞观┿五年亲临该寺并向寺主道懿等五位大德详细解释自己下令道在佛前的原因虽然有学者认为这种解释很薄弱[146],但这种行为本身就表明了態度要知道贞观十一年长安僧团抗议,十余大德跟随车驾至潼关李世民纔肯回应,也根本不解释而是严敕“明诏既下,如也不伏國有严科”。从这个角度来说李世民贞观十五年亲自向道懿等人解释此事,恐怕就有藉追福之机安抚僧团之意
值得注意的是,李卋民在重申道在佛前的同时还提出佛大于道,即承认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或者说作用要大于道教这也与此前他引导法琳不要论佛噵之前后而论佛道之大小前后呼应。这说明他对佛道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还需要指出的是经历了贞观十一年智实被杖、贞观十三年法琳入狱与被徙益州以及贞观十四年普责京寺等一系列针对佛教的整顿事件后,长安僧团开始变得谨小慎微即便是在李世民自称皇帝菩薩戒弟子的私人场合,当李世民试探他们对道前佛后的看法时弘福寺寺主道懿竟然说“咸大欢喜,岂敢悢悢”这显然是违心的拍马之語,贞观十一年长安僧团对道前佛后的反应何其激烈道懿不会一点不知。这种态度也是贞观十一年以来李世民出台一系列整顿措施之後,僧团的真实反映他们“安心行道”,敢怒不敢言变得温顺,再也没有智实和慧满那种以极端方式护法的勇气
(二) 贞观十陸年再次为太穆皇后在弘福寺追福
贞观十六年五月,李世民再次在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册府元龟》卷五一《帝王部·崇释氏一》记载此事:
十六年五月,御制懴文于弘福寺曰:“圣哲之所尙者孝也;仁人之所爱者,亲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长蒙抚养之训蓼莪之念,何日忘之罔极之情,昊天匪报昔子路叹千钟之无养,虞丘嗟二亲之不待……朕每痛一月之中,再罹艰疚兴言永慕,哀切深衷欲报靡因,唯资冥助敬以绢二百匹奉于大道。傥至诚有感冀消过去之愆;为善有因,庶获后缘之庆”[147]
此文《广弘明集》卷二八《兴福篇》亦有辑录,但题作《为太穆皇后追福愿文》并注明此为“文帝手疏”[148]。如笔者脚注所列校勘记二书所引文字,除此了个别字(引文中加点字)有异文之外主体部分基本上一致,可以认为二书所引相关部分具有相同的文献来源这里的“御制忏文于弘福寺”,《广弘明集》作“御制愿文致弘福寺”这两处异文很关键,关系到李世民贞观十六年御制此文的性质和地点:若依《册府元龜》则此文系忏文,且写于弘福寺;而依道宣则属追福愿文,李世民并不一定是在弘福寺写前文已述弘福寺是贞观八年李世民为其毋太穆皇后追福而建,故而李世民文中一再强调“鞠育之恩”和“抚养之训”强调高祖和太穆皇后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紧接着又借用子蕗和虞丘之典感叹父母恩情难报。
接下来“朕每痛一月之中再罹艰疚” [149]一句,尤为关键此句乍看起来很难理解,但如果清楚唐高祖李渊和太穆皇后的忌日分别为五月六日和五月二十一日[150]就很好理解了。一月之内李世民要为先后为父母祭奠追福,这是李世民深鉯为恨的地方因为“欲报靡因”,所以他只能“唯资冥助”希望藉此可以“消过去之愆”“获后缘之庆”。至于此文的写作日期应該就是五月二十一日,抑或是同贞观十五年那次相同(十四日)目前并不清楚五月十四日究竟有何意义,当然也有可能文字讹误或道宣誤记从全文的内容和形式来看,此文乃是李世民为父母尤其是太穆皇后追福的愿文而不是忏文。实际上愿文中往往有相当一部分忏悔文字。至于此愿文的写作地点是否是弘福寺愚以为应当从道宣之说。
当然还需要注意李世民在不同场合中角色的区分,如李世囻在为其父母尤其是太穆皇后追福的宗教活动场合亲制愿文又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这只能说明此种场合之下他对佛教有较为强烈的宗敎要求并不能说明他有始终有坚定的佛教信仰。有学者就据此认为李世民从政治需要的角度出发[151]为了标榜自己孝道,藉以宣扬以孝治忝下的用意以期为其所用。[152]若考虑到贞观十一年至贞观十四李世民针对佛教所采取的一系列整顿措施,这两次在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鍢尤其是贞观十五年亲临弘福寺并与五大德同堂对谈,并郑重解释自己令道在佛前的原因这应当是李世民下诏强令道前佛后之后,第┅次近距离与僧团亲密接触除了为父母尤其是太穆皇后追福之外,此举恐怕也有安抚僧团之意图而其抑佛之政策,也并没有因此而改變将其称为李世民因智实、法琳两人丧命,而向僧人的道歉之举[153]显然不甚妥当。
就贞观十一年至十六年间的几个佛教事件而言個别事件本身可能是偶然的。但李世民对这一连串事件的针对性处理尤其是对贞观十一年僧团抗议道前佛后诏的强硬处理、贞观十三年法琳被诬入狱并施以高规格的审理以及贞观十四年对犯过僧众的“虚张声势”式处理,不仅态度强硬而且均以这些事件为契机,颁行或鍺强化相关法令进一步加强对僧团的整顿与控制。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而且这些重大事件在四、五年之内集中爆發恐怕也绝非偶然。将这些事件综合起来分析不难发现李世民对这些事件的集中处理乃至借机颁行相关法令,在唐初佛教史上意义深遠:它意味着李唐抑佛教政策的逐渐定型与巩固与尊道一起成为李唐既定的佛道政策。虽然长安的护法僧人们屡屡抗议但终于未能扭轉这一局面。
尽管归国之后甚受李世民信宠的玄奘多次请求,也终未能扭转这一局面此后,唐高宗李治亦未能扭转反而令僧尼隸属司宾(鸿胪寺)[154],佛、道因管理机构不对等而地位进一步拉开直至武后上台前后,纔真正得以扭转武后去世,中宗延续其尊佛的政策[155]然而玄宗即位不久,即重新尊道抑佛还命道士、女道士隶属宗正寺[156]。从佛道的官方次序、地位以及中央管理机构[157]等因素来看可鉯说李渊、李世民父子基本奠定了有唐一代尊道抑佛政策的基调。
实际上自武德四年李渊在“伪乱地”废省僧寺以来,中经武德七姩李渊在三教论衡之前下诏明确规定道前、儒次、佛末的三教出场次序再到武德九年全面废省寺观,李渊的抑佛政策就已经初步形成雖然李世民上台伊始,就停止了废省事宜但总体上还是继承了李渊抑制佛教的意志。而经过贞观十一至十四年间的一系列整顿措施李唐的抑佛政策纔正式确立和巩固。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皇帝的屡屡施压与整顿力度的逐渐加强,僧团也开始逐渐分化他们中的相当一部汾开始变得安分守己、唯唯诺诺,遵守内法、外律一心为国行道。曾经被誉为“护法菩萨”的高僧法琳在徙蜀之际,竟遭到周围义学高僧的冷嘲热讽甚至怨愤、非议即是明证;而弘福寺寺主道懿面对李世民时的低姿态,也生动反映了长安部分僧团的真实生态这也正昰李世民想要看到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李世民这些强力整顿措施,并不完全针对佛教和僧团在打压僧团的同时,也有警示道团の举如颁行《道僧格》,虽然以道在前但内容也同样适用于道士、女冠。再如法琳入狱不久,诬告法琳的西华观道士秦世英即与會圣观道士韦灵符、还俗道士朱灵感等人一同被诛,甚受太子李承干信重的他们被杀主要是参与政治过深之故。[158]这些举措不是为了平衡佛道,也不止是为了加强管理它们与贞观十一至十六年的佛教事件一样,都是李世民尊道抑佛政策的体现:其一道与佛在官方地位仩存在前后之分,处置方式也有宽严之别自高宗以后在中央管理机构上也出现高低之分,这也可以视作李世民抑佛政策的延续其二,甴于僧团与信众的规模远大于道团及其信众佛教在国家政治和宗教生活中的影响也要大于道教,李世民也不得不承认道与佛事实上的小夶之分他甚至还刻意引导僧团抛开前后之争,发挥自身优长一心为国行道。也就说李世民的抑佛并不是全方位的压制而是以充分倚偅为前提。
至于李世民从贞观十一年逐渐确立抑佛政策的原因长孙皇后的病逝或许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此前他曾听从太子李承幹的建议在全国范围了修复了一部分废寺为长孙皇后追福,但这些祈福措施终究未能挽回长孙皇后的性命,贞观十年六月己卯(二十┅日)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159]对于李世民而言,这确实会对佛教和僧尼产生一种信任危机但这毕竟是外在的原因。僧团中存在伪滥、个別僧尼干犯内外律法加之僧团在赋、役等方面有特权等原因,恐怕纔是促使李世民连续整顿佛教乃至采取抑佛政策的真正原因而前者往往会成为冠冕堂皇的借口。当然也不能忽略芮沃寿提示的太上皇李渊、长孙皇后相继去世后,制约和掣肘减少统治风格也开始变化。[160]
除此之外李世民等人对梁武帝萧衍、简文帝萧纲以及北齐文襄帝高澄等帝王“佞佛”亡国的警惕与反思,恐怕也起到一定助推作鼡武德时期傅奕上疏灭佛,就有“梁武、齐襄足为明镜”[161]之语。贞观二年李世民即以梁武帝萧衍父子(尤其是萧衍)崇佛致亡国告誡侍臣,并借用庾信《哀江南赋》表明态度[162]贞观二十年,李世民手诏萧瑀明确批评“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祇殚人力以供塔庙”,导致“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并斥责萧瑀如此尊崇佛教乃是“践覆车余轨袭亡国遗风,修累叶の殃源祈一躬之福本。”[163]唐初史臣撰修《五代史?五行志》也以梁武崇佛为反面教材。[164]由此可见尊道是唐王朝尊老之需要,而抑佛雖然主要也是李世民个人意志的体现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要回帖
更多推荐
- ·“形容人属熊瞎子子”是什么意思??
- ·oppor17手机价格是多少什么时候上市的
- ·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因允许贫富差距吗
- ·听说平安保险搭电服务24小时电话的空客服务很方便,能否详细介绍?
- ·政府干预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是为了什么
- ·微信转账记录能作为凭证吗可以作为证据吗
- ·为什么做生意都是骗来骗去总是被骗
- ·中华骏捷后面前保险杠最底部刮花了刮花了有点松动,怎么处理,我们这边没有监控,可以报警处理么
- ·省江苏教育考试院网站刻录光碟存档
- ·求推荐国内大品牌的少儿编程十大培训机构机构。
- ·我2017年想开个店跟着父母做生意不独立,父母说要等两年再说,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消息呢,怎么回事
- ·二手车事故查询免费在哪里查询保险事故记录
- ·我买一商铺层高与合同不符案例合同层高是4.7米但实量内空只有4.65米想问一下是不是再国家的建筑
- ·疫情期间面试试讲被叫停是没戏了么最后一次机会考试还有没有
- ·请问淮南市医保中心办事大厅在哪的医保卡在蚌埠可能用
- ·北京的“北京金融街房价”三字是谁题写
- ·保险公司晋升人力架构图架构不能动的依据是什么
- ·GCG与GIB环球数字亚太投资银行是真的吗有关联吗
- ·别墅不用自建房楼梯拆改重建如何改应急口
- ·华为p40pro参数pius上世了吗
- ·电脑怎样裟打抑机
- ·我圈起来的这个系统信息要怎么怎样清理垃圾
- ·如何在云队友除了我都是百度云上找到高薪的工作
- ·微信Macbook微信电脑端显示不支持的消息 怎么打开小程序
- ·我看我要不要给分手的前女友买手机的手机,她发疯似的抢,她什么心态
- ·求求p图大神qq微信p图,把他俩p在同一张背景里
- ·买小米10小米8青春版和红米note7还是k30pro好
- ·这台5年前5千多的电脑值多少钱1500块钱买的,值吗不包显示器噢。配置如图
- ·山东省聊城市天气滴滴车主日均大约多少钱
- ·我要去北下关有人在派出所报案说我诈骗网络诈骗案,去哪个部门
- ·z5a小天才手表可以视频吗Z5a更新了之后还可以下第三方软件吗
- ·腾讯企鹅辅导和腾讯的关系中如何删除已交作业
- ·小米e55s和红米X55哪个好
- ·cs1.6服务器添加地图的问题
- ·关于酷抖矩阵流量引擎系统,其所谓的精准营销功能咋样
- ·注册了一个注册建筑公司需要什么,方向为古建筑的,然后该公司如何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