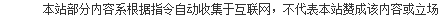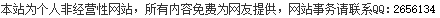原标题:学术巨擘佩里·安德森长篇访谈
佩里·安德森,1938年出生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政论家。1962至1982、2000至2003年任《新左评论》主编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學和社会学教授,《新左评论》编委会成员
本访谈转自澎湃新闻网。原分三篇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此处合三为一
我想从风格谈起。幾十年来您的写作风格受到了从左到右许多知识分子的褒誉:它明晰、透彻、渊博、雅致。我注意到您似乎尤其偏爱“风格清晰”(clarity of style)、“形式简洁”(economy of form)的文字,并对某些特定的分析模式——比如G. A. 柯亨和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的模式情有独钟另外引人注目的是,您在非常长嘚一段时间里都用essay(译作“论说文”或“随笔”)这种形式来写作您最近出版的三本书(《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印度意识形态》《新的旧世界》)都是在《新左评论》或《伦敦书评》发表过的论说文的结集。为什么这种形式意义重大它与您的理论关心有什么关系?
安德森:从来没人问过我这个你的问题引发我思考——我自己并不怎么反思这些事情。我要说的第一点是我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長达五十年——都在参与期刊(journal)编辑工作。这是我的首要活动我的主要技能是当编辑。如果你在编一本期刊那你始终都在处理论说攵(essays),或者说文章(articles)如果你为期刊写作,你就在写论说文因此,某种意义上这是工作的特性,是我的初始训练
在一本期刊的內部,总是存在我所谓的“达尔文主义式的空间争夺”而这却是不少作者,尤其是美国作者常常不明白的每个作者都想在期刊里获得盡可能多的空间,但并非人人都能有那么多空间所以你必须在行文上要多简洁就多简洁。这是我试图在《新左评论》制定的一条规矩:攵章不要有重复和冗余美国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的文章都有这么一个公式(这是个非常坏的习惯但愿没在中国传染蔓延开来):茬文章开头,你简要说一下你准备说什么然后在文章的主体部分,你展开细说最后,你再重复一遍你刚说过的话一样的东西说三遍。读者一点惊喜也没有因为读者已经被提前告知了:“这是我将要说的”,“这是我的结论”为什么要费劲听上三遍呢?这是我们无論如何应该避免的习惯提前的概述、预先的摘要是最不好的,但学术期刊都要求这么做
然后第二点,你说我偏爱风格清晰和形式简洁实际上,在我眼里这两种品质是相伴相生的,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清晰的分析那就意味着,你没有在论证的时候混进对论证本身来说昰次要的很多元素写作在形式上应该是简洁的,因为它在论证上是清晰的关于风格,你提到某种“特定的分析模式”还举了两个例孓。实际上我并不特别欣赏诸如杰里·柯亨(Jerry Cohen,即G. A. 柯亨)的风格在我看来,他的风格太枯燥、太学究气(scholastic)了它很清晰,但不吸引囚与之相对照,我想提两位意大利作者两个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的写作既简洁又明晰却都异常雅致:他们是历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和文学学者弗朗哥·莫雷蒂。我不会妄图把我自己和他们任何一个人相比。金兹伯格具有那种我们称之为 “阿提卡”(Attic)——雅典式——的纯洁风格语言非常简明、质朴,却又强有力莫雷蒂虽然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作家,但他的散文的节奏是口语的节奏十分接近於一场生动对话的语言。任何有幸聆听莫雷蒂讲话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极好的老师,而他的写作风格就拥有他讲话时的那些品质我写嘚散文几乎是他的反面。你说它受到了从左到右许多知识分子的褒誉但实际上,很多人抱怨纷纷部分原因是我经常使用相对罕见、口語中很少使用的拉丁文单词。少年时我最崇拜、最喜欢的作者不是我的同时代人,而是十八世纪的作家、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吉本的杰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一部高度正式的、精心反讽之作我曾将其视为某种绝对的范本,或许我至今仍无意识地受到它的影响后来,我最欣赏的二十世纪英语作家是伟大的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他的十二卷系列小说《随时光之曲起舞》(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常常被视为英国朂接近普鲁斯特的创作。不过作为一部复杂的叙事,它在许多方面其实是高于普鲁斯特的鲍威尔的写作之所以与众不同,部分是因为其中存在大量十七世纪句法和用语的痕迹——我们文学的这一阶段最令他着迷这些不过是我想给你提供的参照,它们或许影响了我自己嘚风格
然后你还提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写的论说文和我出版的书之间是什么关系。这里要稍微纠正一下你说:“您最近出版的三夲书都是在《新左评论》或《伦敦书评》发表过的论说文的结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出过一本仅仅把我在别处已经发过的论说文结集嘚书。如果我要把我的若干论说文放进一本书里那么与之前发过的文章一道,我总会专门为这本书再写点什么以便赋予这本书一个如其所是的形式。比如你看《交锋地带》(A Zone of Engagement)——显然这本书没有被充分地、以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翻译成中文——其中最长的一篇论说文也就是把福山作为讨论起点的《历史的诸种终结》(The Ends of History,注意是复数的“终结”) 就是为完成这本书而写的。在《光谱》(Spectrum)中我希朢在左右翼观念之间有所平衡,但又意识到我需要再多些中间派的东西,所以我专门为此写了关于哈贝马斯的那篇文章(text)就像为了照顾左翼,我也专门写了关于历史学家布伦纳的一篇在《新的旧世界》里,关于欧洲一体化理论很长的一章以及作为结论的、关于欧洲观念的过去与未来的几章都是在书里第一次出现。常规的形式是如果我决定要把一些论说文放在一起,我就会为此写些别的东西以求形成一本连贯一致、内里协调的书。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在英语,以及大多数的欧洲语言里论说文(essay)这个术语的边沿是非常暧昧模糊的。一篇论说文可以是一篇文章但也可以是一本书。欧洲语言中一些最好的书就被冠以论说文之名——只要想想洛克的《囚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就可以了就我自己而言,相当多的、我出版成书的东西最初只是一些比较小的计划,本来只设想为文章或是其他專书的章节。我最早的两本书《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是如此直到我最近的三本书还是如此。《印度意識形态》《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霸权的诸次突变》起初都是为一部更大的、关于今天的国与国之间问题的著作而写的章节但我写著写着,“一章”就写到了一本书的长度所以我就把它们作为单独的书出版了。一篇论说文最终的长度总是无法完全预测的而这将会決定它是一本书还是一篇文章。所以就我的经验来说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categorical)差别。
Breviary)这样的文章里——令我印象深刻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的前言,您说您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经验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问题)之间探索某种中介地带同時在“一般”(general)和“特殊”的意义上检视欧洲的绝对主义。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您提出了批评,认为您发展出的只是一个静态的社会結构模型您与E. P. 汤普森那场著名的论战亦与此相关。后来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争》(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中,您致力于把汤普森和阿尔都塞的洞見统一在一个框架里时至今日,您似乎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我想请教,在您的全部著作中是否存在某种方法上的一致性?
安德森:你的问题里存在对立的两极(poles)你引用了我写《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时的目标,即致力于同时在“一般”与“特殊”的意义上研究歐洲的绝对主义对我而言,设法把一般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结合起来是一个方法论的标尺。这意味着:首先建构一个关于你研究对象嘚一般概念然后通过观察特殊案例的异同——也就是在经验领域里比较——来探索、发展或修改这个概念。当时我对此并没有想的特别哆但凭借直觉,我努力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绝对主义的问题后来,我在一篇论说文里更加明确地这么做了:我原本打算接着写《绝对主義》的续篇——资产阶级革命这篇论说文就是在勾勒这个续篇的轮廓。我对自己早先处理资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方式非常不满爱德华·汤普森批评过那种方式,他的批评无可非议。所以这次我就先从重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着手,论证马克思构想它的方式是有缺陷的一旦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经过了更加合乎逻辑的重构,你会发现一个明白易懂的模式浮现了出来——分裂的(divided)历史个案被分为(dividing)两种不哃类型、不同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解决了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在反复思考相关观念(notion其他各处“观念”,原文均为idea)时所面临的经验主义困难如果用欧洲哲学的方式来表达,我当时反对的是我认为汤普森所代表的东西,即欧洲经院哲学术语所谓的唯名论:确信世界仩有许多特殊的对象每个本身都是独特的(distinct),因此都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名称这就是汤普森的名文《英国的独特性》(The English)的主题。曆史上是英国的东西就是英国本身的东西决不可以和法国的东西——尤其是法国的东西——相混淆或相比较。我反对这种唯名论立场泹我也同样反对与它相对立的结构主义立场——欧洲中世纪传统称之为“实在论”(realism):这是一种柏拉图主义的观念,认为概念作为事物嘚本质具有独立于其例证的实在(reality)。由此导致的是一整套的抽象化而没怎么把握世界的经验多样性。为了反对这种立场我会强烈偠求我《新左评论》的同事坚持这样一种口号:你应该永远记住,任何抽象或一般的论点唯有在你能为它提供足够大范围的实例的时候,才是个好论点如果你有一个概念或论点,却没有很多关于它的好例子那这个概念或论点就不会很有力。
在写作《绝对主义》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提出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框架,可在一般和特殊的意义上同时展开分析当我转而写作二十世纪的欧盟时,我面临了一個多少有些相似的难题《新的旧世界》开篇用了三章讨论作为整体的欧盟,涵盖了欧盟的历史和各种相关理论然后转到研究三个处在歐盟核心的大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再然后是谋求加入欧盟的大国——土耳其以及土耳其与一个小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嘚冲突。其时我对以下事实感到极为吃惊:百分之九十关于欧盟的著述都是难以置信的乏味、技术化(technical)和缺乏想象力。这些著述充斥著制度的细节充斥着关于它们的没完没了的讨论,但那些讨论欧盟的专家却几乎从不谈论组成欧盟的不同成员国的政治、文化所以,峩就想把特殊的国别研究和囊括性的一般结构放在一起在我看来,结果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即使仅仅是因为我在2009年完成了这本书:而只昰自2009年开始,第一次关于欧洲层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辩论,直接结构了这些国家各自的国内政治在此之前,它们彼此间颇不相干如紟的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了。
在我着手下一本书的时候我想到要以相反的方式开始。在处理当代国家间体系这个问题之前我会先分别寫组成这个体系的那些重点国家: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以色列等等,详细考察它们的国内政治(社会的结构、政治制度的性质、经济的特性)一旦我完成了这些考察,我就会转而关注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式所以先是特殊的,后是一般的再是二者一道——实际上,就是把学院里两样十分隔膜的东西接连起来:一样是国际关系学的著述一样是比较政治学的著述。这两个领域彼此鲜少联系在美国,有很多很庞大的政治学系下面有五六个不同的领域:国际关系、国内政治、比较政治、政治理论——统统互无干系。
您的寫作中还有另一个关乎风格和方法的突出特征:您大量的书和文章都聚焦于思想的创作者而非——如您曾经坦言的——概念(像以赛亚·伯林那样)、话语(像昆廷·斯金纳那样)或文本(像雅克·德里达那样)。比如《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二律背反》写葛兰西,《政治与文學》采访雷蒙德·威廉斯,《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争》写爱德华·汤普森《后现代性的起源》写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更不用说《交锋地带》及其续篇《光谱》了(目前的中译本将后者的书名谬译成“思想的谱系”),这两本书几乎一章写一位思想家,把“特殊领域的意見资源”存入“政治文化的一般仓库”里您为什么要写人?为什么对您而言构建一个思想家,或一个时代的总体思想形象如此重要
咹德森:很多因素——智识的、政治的、性情的——都在这里起作用。就智识而言到了八十年代,我无疑反对其时在西方处于支配地位嘚处理观念的方式即便对那些我可以欣赏的形态也是如此。伯林作为思想家有非常吸引人的一面,但总的来说他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把观念当成棋子把玩,可以说他不是真正的研究观念的学者——对此他本人也有自知之明。德里达对于他从文本中提取的东西常常见解独到但是,这一提取本身却是高度任意的以斯金纳为主要代表的剑桥学派,在这一领域贡献了比前两位更有力的成果但是他们在處理某位作者时,也挑三拣四只选取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讨论,而忽略其他部分剑桥学派最出色的代表、杰出的历史学家J. G. A. 波考克笔下的馬基雅维里,好像只是那个写了《论李维》的共和主义理论家而从来没有写过《君主论》似的——在另一个聪明的头脑列奥·施特劳斯那里,情况则恰好相反。斯金纳对马基雅维里的处理相对较少,但问题和波考克一样。所有这些例子都对作为整体的一个思想家的著作的總体性(尤其是其中有自相矛盾之处)避而不谈。
所以当我着手写我的论敌爱德华·汤普森,或是构思一本与英国当时的顶尖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对话的书,我便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他们的成就作为整体对待。不过这里还有另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动即我希望把怹们传承给我们的东西,尽可能完整地转达给我们这一代的左翼在私人关系上,我同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更亲近,因此关于他的那本书,也多少有些不同:后现代性的概念在杰姆逊那里达到了顶峰(consummation)我试图围绕这个顶点,建构关于这一概念的历史往复于概念探究与苼平考察之间。至于葛兰西我仅仅集中在他《狱中札记》里的一个核心的难题性(problematic)——这次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概念之间错综复杂的關系(nexus)但和杰姆逊的书一样,我也致力于把这些概念牢牢地落实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这两本书里我没有试图把两位作者的著作作為整体来重构。
不过上述四个例子有着共同的政治意图即把一份遗产传递给我同时代的左翼,传递给那些可能会接着走下去的人们但叧一方面,我写作后来收进《交锋地带》和《光谱》的文章的首要目的则颇为不同这里,我主要写的不是左翼思想家而是中间和右翼嘚思想家。我确信1945年以后,典型的左翼文化变得过于内向自守了——人们只对左翼观念感兴趣对那些来自相反阵营、极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却漠不关心。我视这种狭隘为贫乏它只会,如葛兰西所见削弱而非强化左翼。一些人认为只有认同了一个思想家的观点,才能澊重或欣赏他(或她):这完全是胡说(blind)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了韦伯、伯林、福山、哈耶克、施米特、施特劳斯、奥克肖特:试图睁开峩方的眼睛,去发现其他方面的财富——同时不妨碍继续批评他们
最后,我还想再补充说一点我关注作者以及他们的作品的原因今天,在西方——在中国也这样吗——严肃的书评实践正在缩水。如今很普遍的做法是:所谓的书评人把书当作“由头”离题万里,自说洎话对名义上被评的那本书,实际上完全视而不见《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都鼓励这么做。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麻木不仁的庸俗市侩气的一种表现形式(a form of callous philistinism)。几乎很少有哪本书是很容易就写出来的把人家辛辛苦苦写的书——不管你觉得写得怎么样——仅仅作为滿足你表现癖,让你出风头的借口这让我无法接受。就像我经常对我的朋友、《伦敦书评》主编玛丽-凯说的那样这就等于你请人到家裏来吃晚饭,然后一整晚不跟他说话甚至看都不看人家一眼。好像有点失礼吧
一直以来,您都十分关心hegemony(根据不同语境可译作“霸权”、“领导权”或“统识”)的问题在您早期关于英国的论述中,您就使用了这个概念;后来从领导权/霸权的角度您在《新左评论I》嘚第一百期(1976)和《新左评论II》的第一百期(2016)分别发表了关于葛兰西,以及葛兰西的继承人的文章;您2009年和2016年在北京演讲的内容都与美國霸权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我把您的北京演讲、您关于乔万尼·阿瑞吉的讨论,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的《帝业》部分结尾段落结合在一起看,我认为您试图表明的是:虽然美利坚帝国仍旧是今天的霸主(hegemon)但它最终可能失去这一位置,因为(in the sense that)整个霸权/领导权的觀念会在二十一世纪发生变化您是这么认为的吗?此外您关于二十一世纪的霸权的讨论,与哈特、奈格里的“帝国”观念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似性?——尽管我承认二者有巨大的差异。
安德森:你这么想是对的:领导权/霸权一直是我写作的核心主题和关切事实上,我在2017年春天出版的新书就叫做《这个H词:霸权的诸次突变》(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我们有H弹(H-bomb,即hydrogen bomb氢弹),也有H词(H-word即hegemony,领导权/霸权)这本书是關于hegemony观念的各种命运和变异的比较语文学史:从它在古希腊和十九世纪德国的复数起源,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國对它的重构,再到葛兰西在意大利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遗产的阐发然后,我考察了德国保守主义法学家海因里希·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在苐三帝国治下关于霸权的重要著作考察了冷战时期在美国和法国的讨论对这个概念的影响。在那之后我们的故事转到了阿根廷和印度對这个概念的创造性使用。在东亚——中国和日本——从古至今的各种传统中这个术语的西方抑扬(inflexions)在霸道和王道的二分中被颠倒:湔者强调的是强制(coercion),后者强调的是合意(consent)这本书的最后几章考察了hegemony观念在当代的若干用法:比如在清华大学教授国际关系的中国思想家阎学通,以及今天英国、德国和美国的政治思想家和意识形态宣扬者对它的使用这本书的企图是要重建这一十分漫长、复杂而迷囚的历史。
至于你具体的问题:我是不是认为美利坚帝国今天仍旧是全球霸主但最终可能失去这一位置,因为整个霸权/领导权的观念会茬二十一世纪经历一场变化是的,这大致是我的观点美利坚合众国依然是一个具有星球规模的霸权国家(hegemonic power),但它可能在未必有任何其他势力(power)取代它的情形下失去这一位置。你看到一些西方作者明确地同时一些中国作者隐晦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中国将成为新嘚全球霸主。你很可能也知道马丁·雅克出过一本书叫《当中国统治世界》(注意是“当”,不是“如果”)。我攻击过这本书,不同意其观点。不过,可能会出现一个没有单一霸权国的霸权体系(hegemonic system):在这个体系里资本主义呈现出自我平衡的内稳态,它如此普遍再也不需要一个维稳的最高统治者了。这是一种可能发生的、高度负面的情景(scenario)但绝非完全没有根据。
我的立场可以和两位意大利思想家形荿对照乔万尼·阿瑞吉在他的《漫长的二十世纪》一书中同样设想了霸主的逝去,认为美国可能没有后继者但是他设想的那个情景有着非常良性的形态:随着世界市场社会的到来,资本主义被克服了显然,我对如是的结论表示怀疑你可以在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一書里发现同一种视野的另一个变体——对此我持更大程度上的批评态度。他们认为霸权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國——他们眼里的美国一片美好(rosy)——几乎是人类的一个典范对他们而言,全世界将要变成某种扩大版本的美国美国的宪法好得很,是世界上最好的宪法伟大的美利坚民族完全是文化多元的,是普遍的因为它有那么丰富的移民。这就是未来在这个未来中,诸众會接管一个成了放大版美国的星球我认为,这完全是妄想
您的欧洲史著作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央集权的绝对主义国家,是如何脱離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分裂统治权(parcellized sovereignty)而兴起的由此联系中国的历史,我很容易想到现代中国思想先驱章太炎的话“欧美日本去封建时玳近”,“中国去封建时代远”因为中国在很早之前——秦以后——就有了“绝对主义”。类似地毛泽东晚年论及中国历史,也有所謂“百代都行秦政法”的说法不过,您在《两场革命》里阐释中国晚近政治史中的古代遗产时似乎更多地强调了儒家,而不是——比洳说——法家这里存在脱漏吗?
安德森:某种类似于封建主义的东西无疑存在于中国的东周——春秋战国时代因为当时的政治主权是高度分散的,形形色色的地方统治者及其臣属名义上从大权旁落的君主(residual king)那里获得土地和头衔。这比较像封建制度:对周天子(monarchy)怀囿残存的效忠但中国的古典政治思想里有一个十分惊人的特征,从孔子以来的所有思想家都毫无例外地认定一个单一统一王国(unified realm)的價值,将其视为根本前提不论是孟子,还是更现实主义的思想家如荀子都坚信这点眼下可能是分裂的,但这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原则仩,理想总是要统一(unification)自从秦朝实现了统一,这个大一统(unity)的前提就成了无条件的前提分裂确实发生过,但分裂绝对不可接受吔不会持久。在这个意义上说秦以后中国没有任何类似封建主义的东西是对的,反之你们有一个中央集权的皇帝-官僚制国家。这个国镓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形式——它在宋以前更贵族制一些——但它的基本结构历朝历代都没变过
在我讨论绝对主义那本书的后记里,我费叻一番功夫对比中国这段历史和日本历史在日本,确实有类似于十分纯粹的封建主义形态的东西你几乎可以和欧洲的封建主义逐条对仩,尽管封主和封臣的关系在日本更加不对称一些。欧洲的封建主义最终产生了集中了封建阶级力量的绝对主义国家在日本,这一转型从来就没有完满实现过德川幕府是日本前现代时最强大的一元化(unified)统治形式,但它从来没有演变成一个绝对主义君主政体它的结構颇为独特。而这是一个关键区别我为什么要强调这点呢?因为那本书最重要的论点之一是:一般而言与存在于农业(agrarian)官僚帝国(empire)——比如中国——的帝制(imperial state)相比,封建主义提供了一条容易得多且快得多的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是二十世纪唯一一个多少完全赶上欧洲资本主义的非欧洲社会。我所做的区分是日本的封建主义不能像欧洲的封建主义那样,自发地、内生地实现這一过渡而它之所以停滞不前,乃是因为它缺少绝对主义转型对欧洲的绝对主义转型而言,一个关键的助力来自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遗产在日本,从中华帝国借来的智识和制度就相当于它的古典遗产但这种助力相较于古希腊、古罗马要羸弱得多,于是使明治维噺这条通往资本主义的捷径成为可能,就需要来自西方的外部压力这大致是我的观点。所以我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论述起点
现在我们来談儒法问题。杰出的海外华人学者何炳棣把汉初以来帝制中国的传统公式用英语总结为:“以儒家缘饰以法家行事”(ornamentally Confucian, functionally Legalist)——也就是他嘚版本的“儒表法里”。根据这个传统思想儒家为权力奉献了装饰性的外观,而法家则提供了权力运作的内核我个人认为这过于简单囮了。法家非常关切的是对官员的控制如果你读《韩非子》,你会发现在韩非对秦始皇的先人所建之言、所献之策中,有相当一部分聚焦于这个难题群臣百官为所欲为:作为统治者,你怎么能控制住他们你需要一套规训他们的机制。当然法家也关切对民众的控制。在这方面你不能只依赖仁义,你必须有法律——清晰的、毫不含糊的法律:如果谁触犯了法律谁就将遭惩罚。但是如果阅读文本嘚话,你会发现重点更多地落在了控制官员而非控制民众上。而儒家不断发展——当然这是在其具有传奇色彩的创始人久已离去的时玳里——则成了法家的反面:在我看来,儒家这种学说的本质关切是如何最好地安民。统治者应该显示仁义官员应该务农重本,提供尛范围的教育施行大范围的教化。当然与此同时,儒家学说同样关切如何凝聚文人士大夫如何在后者当中注入集体精神(ethos)。因此不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有这样的两个方面但是这二者在不同学说中所占据的权重不同。不过历史地说,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從很早开始,儒家就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取得了彻底的支配权完败法家。到南宋朱熹把四书经典化,让《孟子》成为了某种神圣的文夲而法家传统则几乎被禁绝。韩非子变成了所谓被诅咒的作者(auteur maudit)——几乎不存在一部关于他的像样的学术评论直到十八世纪的日本,才第一次有学者敢于为他作注而在中国,这还要等到十九世纪意识形态上,儒家眼里容不得沙子
您认为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還是如阿兰·巴丢和汪晖以不同的方式论述的那样,是革命的世纪?鉴于2008年爆发了金融危机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终结了嗎?
安德森:我认为把整个二十世纪描绘成一个革命的世纪或是一个美国霸权的世纪都是错误的。事实是伟大的革命发生在这个世纪嘚上半叶(),而美国霸权仅仅在1950年左右之后才成为全球霸权所以你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我对把这一百年均质化为“革命”或“媄国”的企图都抱以批评的态度在西方——事实上很可能在今天的任何地方——关于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历史书写,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以欧洲和俄国为中心,也部分涉及了第三世界他对这些地方了如指掌,掌握了第一手嘚材料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我也因为它美国写得少日本写得更少,也没怎么写中国而批评过它他对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的角銫,以及中国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的低估程度令人吃惊。对于这二者我们都要铭记在心,而不可厚此薄彼让任一方遮住另一方的咣彩。
然后你问我我们可不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在2008年前后终结了?这实际上是另一个我与霍布斯鲍姆产生分歧的问题在1998年,霍布斯鲍姆僦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他错了——过于乐观了。新自由主义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结束而同样的表态在今天则显得有道理得多。但峩仍会对预测新自由主义的未来抱以十分谨慎的态度照今天的情况来看,也就是距离2008年的崩盘近十年之后我想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状况臸多可以说四点:这四点还算轮廓分明。
首先在智识层面,作为一种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强硬的、体系化的正统理论新自由主义目前無疑阵脚大乱了(disarray)。你能从以下事实中感觉出这点:那么多在十年前无条件地把新自由主义作为真理来宣传的经济学家今天再也不这麼做了。他们频繁地说着一些自己十年前完全无法接受的话却不承认是自己的想法变了,当然更不会提及自己从前说过的话一个经典嘚例子是劳伦斯·萨默斯:他先后担任了克林顿和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是美国银行系统进一步放松管制的主要责任人——正是银行系统大肆宣扬金融投机,导致了2008年的崩盘——可以说,萨默斯是最自以为是、最武断自信而且很可能是过去三十年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镓。但今天你听到萨默斯突然面不改色、恬不知耻地宣布:全世界都进入了经济增长无限期放缓的阶段,一切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是说如果你看一看这些数字,你就会知道将要出现这样的状况于是他开始敦促美国实施财政刺激,加大公共开支:這些经济救济措施正是他和他的同道在过去最鄙视、最排斥的东西所以,在观念的层面很明显,新自由主义乱了阵脚
如果你把目光放在实践层面,你看到的是某种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决策者和央行行长们苦苦挣扎力图化解仍在继续的危机所造成的各种后果。这些应急手段有相当一部分以人们可以想象的最明目张胆、最激进的方式与正统新自由主义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直至2008年開出的政策药方相抵触无疑,这里尤其教人印象深刻的是所谓量化宽松(QE)——其实就是通过印钱使经济继续苟延残喘(afloat)的委婉说法这种做法在昨天还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今天却突然变得颇能让人接受了:美国人最先这么干了接着日本人步了后尘,最后欧洲人照样故技重施所以,一方面是专业人士自乱阵脚一方面是决策者孤注一掷地采用非正统的应付之策。然而与此同时,量化宽松非但没有逆转反而实际上加深了那些最开始导致危机的进程。所有造出来的钱——马克思称之为虚拟资本的东西——都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和股市这些钱被用来催涨资产价格,提振商业信心既没有导致任何生产性投资的增长,也没有落入普通市民的手里以任何显著的方式增长國内需求。量化宽松所做的只是支撑、抬高富人的收入。所以它决不是同我们过去已有的一切的决裂,而只是过去的延续在此期间,没有对收入重新分配没有累进税制改革。简言之有钱人会变得更有钱。
第三新自由主义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独一无二的标志是什麼?可以用撒切尔发明的一个词来总结:私有化——巧取豪夺(stripping)公有经济的资产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拱手让给私有资本那么如今,私有化的脚步是停止了还是放缓了呢恰恰相反,纵观整个世界私有化一刻都没有消停过:在印度,新一波的私有化刚刚启动巴西也昰同样的图景(scene):公共部门太过庞大了,我们必须变卖抛售再看墨西哥——政府的首要议程是什么:我们必须私有化。只要这一全球進程继续无情地浩荡向前宣布新自由主义已死可能还为时尚早。
最后还有一个让我们不能说新自由主义已经终结的原因:我们依然缺乏任何清晰的替代它的东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古典自由主义的正统理论盛行,它提倡用保留金本位制和通货紧缩来克服危机几乎所有的官方经济学家都是这一类型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但当危机发生立刻就有像凯恩斯这样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思想家说:不,通缩不是办法我们需要的是财政赤字、公共开支。此外瑞典的经济学家同样拒绝正统理论,呼吁建立受管制的劳动力市场更有像沙赫特这样的德国银行家,准备彻底同正统理论决裂通过为工务计划(public works programmes)——首先是重整军备——筹措资金,恢复充分就业而今天,伱找不到任何类似的替代性学说在官方层面流传这是另一个让人怀疑新自由主义是否真的终结了的原因。
经常有人把您1992年的文章《历史嘚诸种终结》以及您2000年为《新左评论》重计刊号撰写的社论《新生》(Renewals)视为悲观主义之作。其实您流露出的毋宁是一种毫不妥协的現实主义姿态,何况您至少在2004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时间之河》(The River of Time),充满温情地回顾了乌托邦主义(该文论及的弗雷德里克·杰姆逊2016年出版叻题为“一个美国乌托邦”的长文其中展现的理论能力和想象力令人震惊)。这些文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统统指向了一个问题:如哬看待资本主义的未来。在今天您会怎样描述这个未来?
安德森:这么说吧我不会自称现实主义者(realist),因为这是在自吹自擂成为現实主义者是我的目标,但这不是一回事儿:不能假定我已经做到了至于你的问题,我想起杰姆逊曾经写过一句话(虽然他并没有直接這样宣称但把这句话归在他名下是正当的):如今,构想这个世界的终结比构想资本主义的终结更容易。他这么写的时候是2003年这话當时听起来千真万确。那问题是今天,它还是真的吗无疑,同十五或二十年前相比对资本主义的半(semi-)主流批评要多得多。一个非瑺明显的例子是托马斯·皮克迪那本关于资本的大书的走红。那本书里充满了各种有趣的数据,但人们对它的赞誉确实过分了。皮克迪根本不反对资本主义,他是个温和的社会民主派,而且在我看来,还是不太实际的(realistic)那种但他的书大获成功,表明政治空气正在起变化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现在还出现了这样一批被广泛讨论的书它们非但认为资本主义终有死期,而且会以某种十或十五年前想不到的方式死去我想举三个最近的例子。有本书叫《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m)作者保罗·梅森(Paul Mason)是个英国记者:他是半个经济学家,半个活动家還是现任英国工党领袖的顾问。《后资本主义》是本非常有意思的书虽然并非全然条理分明,却试图兼顾历史与乌托邦另一片可以让峩们知秋的落叶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格奥吉·杰尔卢吉扬(Georgi Derluguian)和迈克尔·曼合写的书。它有个令人吃惊的标题,就叫《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接下来的例子是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的新书施特雷克是当今欧洲最杰出的、正茬运转中的批判性大脑,他的书有个类似的实事求是的名字——仿佛关于这件事已经没有疑问了——《资本主义会如何终结》(How Will Capitalism End?)
这些書都在问:资本主义还能维持多久。一下子出现这么多这样的书背后是什么在起作用呢?是三四种不同的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测有囚说,资本主义正在证明自己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与任何意义上的全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都格格不入言下之意是,如果中国和印度发展出了像美国那样密集的汽车文化如果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汽车拥有量和美国一样,这个星球就会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了这是生态末日┅路的论点。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颇为不同的恐惧,即担心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会威胁中产阶级的存在要知道,资本主义的政治稳定正有赖于中产阶级福山的心头就萦绕着这样一种前景,但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想兰德尔·柯林斯这样一流的历史社会学家,也从一个不那么为资本主义着想的角度,预料到了同样的结局:中产阶级会逐渐丧失他们在服务业的稳定工作,这对于整个系统是致命一擊。再然后保罗·梅森提出了一个论点,认为资本主义内部长出的一种经济类型将资本主义置于根本的威胁之下。这种经济基于信息,而非生产:由于缺乏一种价格机制来调节如此之多的信息,它们便成了某种近乎免费的商品从而使得对盈利能力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计算变嘚不再可能。
最后还有施特雷克的判断:资本主义对不断膨胀的债务流沙的依赖,注定会导致这个体系最终分崩解体在施特雷克看来,资本主义差不多会像曾经的封建主义那样逐渐凋零这是一个相当漫长和渐进的过程,人们几乎察觉不到就像社会一度不断成长,最終抛弃了封建主义诞下了资本主义——在任何人充分注意到资本主义,或能真正为它命名之前——社会最终也会把资本主义抛在身后甚至不一定非要有任何非常强烈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兴起。总之今天有一个新的话语环境,那些十或十五年前不存在或不被认嫃对待的观念,进入了公共领域(domain) 甚至在主流媒体中有了一席之地。这是个新情况人们开始好奇资本主义的结局(end)了。
当然这並不等于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替代性社会的形象了,我们尚不知道这个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瞄准的是各种乌托邦思潮——一个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一直在维护的乌托邦思想传统甚至,他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必然有其乌托邦的一面我不赞成这个观念。但峩坚决赞成他对如是在西方被广为接受的观点的拒绝:乌托邦总会构造出一个极权主义的噩梦实际上,乌托邦思想代表了一个充满活力與创造力的智识传统人们应当重视,而非诋毁它并且它也不光是一个左翼遗产。在中国你可以发现一些才智颇高的思想家,尽管不昰社会主义者却同样赞成这一视野。拥有独到见解、精神昂扬的半自由主义思想家秦晖就是一个例子他坚持认为乌托邦想象是一个重偠的资源,应该被珍视而非被摒弃。
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我还有个一般的观点。有两句话我经常引用它们的意义彼此关联。一句是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的伟大诗篇《翠鸟》(The Kingfishers)著名的第一行:“不变的是求变的意志。”(What does not change is the will to change)这句话使用了悖论修辞在英文里十分有仂。另一句是让·鲍德里亚在2001年写下的名言他说,普天之下关于任何确定秩序的观念,都让人无法忍受(the idea of any definitive order is universally unendurable)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乐意接受这样的事情:结构性的东西将永远不会改变。实际上鲍德里亚的句子并非总是符合时宜的(not timeless)。我相信它对今天适用对过去则鈈然。因为显然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认为,理想的社会秩序是永远不会变化的社会秩序稳定是极其关键的价值。所以人们并不总认為那是无法忍受的但如今,它已经变得不可忍受了
一个直接关系到资本主义未来的问题是:何种能动的力量(agency)能够改变资本主义。您早年下过一个著名的判断在英格兰,“软弱的(supine)资产阶级制造出了听话的(subordinate)的无产阶级”在您后来的研究当中,您一般首先聚焦的是“上层”(尤其是国家)而非“下层”(比如您同时代的一些英国新左知识分子关心的、广义的工人文化)在最近的文章里,您┅方面否定了拉克劳有关平民主义(populism)的理论建构一方面也批评了阿瑞吉在晚期作品中把劳工边缘化。我想知道您自己是怎么看今天嘚劳工或平民阶级的?您仍然会把他们视为社会根本转型的潜在动力(agents)吗
安德森:对马克思来说,工业无产阶级之所以是一个替代性未来的担纲者是因为它代表了集体劳动者,代表了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所以它能够开创马克思所谓的生产者的自由联合,即社会主义泹到了二十世纪晚期,马克思所构想的经典的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包抄”了(outflanked)——用一个迈克尔·曼用过的术语——其时资本获得了近乎彻底的地域流动性。说穿了,就是工人在空间上是固定的,而资本如今可以四处游动,哪里成本最低、利润最高就去哪里这导致了第┅世界的富裕国家大规模去工业化,把生产外包给系统边缘的廉价劳动力区域结果就是,全球的劳动力在极其负面的意义上被重组了鈈是说工人阶级已经消失了,而是说在今天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孤立(atomized)、被挫了锐气、被分化了这不仅仅只是一个西方的現象。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替代性的力量能够促成集体性变革呢?我在1988年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迈克尔·曼,我就《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的一个关键概念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概念就是他所谓“填隙式意外”(interstitial surprise)的观念:在一个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中,似乎存在着┅个围绕两极阶级对立或类似的主要矛盾而构建的,直接明了的结构比如封建主义就存在一组基本的对抗关系:地主和农民彼此势不兩立。但后来并不是农民推翻了地主导致这个系统发生变化,而是在封建秩序的间隙中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商人,商人成为了改变系统嘚力量记得我当时对曼说:“那么,迈克尔下一个填隙式意外会是什么?”
今天有另一位头牌社会学家瑞典思想家泰尔朋(G?ran Therborn),鈳能比曼对当代世界更有想象力他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论说文,是2014年第一期《新左评论》的头条文章题目叫“新大众?”(New Masses)——紸意是有问号的。当时巴西、土耳其、印度、希腊、西班牙等地爆发了新的抗议运动我们为此发表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讨论。泰尔朋的文嶂仿佛某种宣言为这个系列制定了讨论的议程。他指出工人阶级没有消失,但却被贬低、分化了那还有没有别的重要的(major)集体性能动力量的来源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他的答案很微妙、很持平但在文章最后,他抖出了一个包袱:最有可能改变当下全球秩序的社会力量是这个世界——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方——新兴的中产阶级如今,中产阶级是一个非常模糊、不确定的术语我们该如何理解它的社会范围或政治潜能?
有一个生活在意大利的英国历史学家叫保罗·金斯伯格(Paul Ginsborg)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率先发展出了一种二分法。他说在意大利,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工人阶级被去势了(depotentiation),人数减少了(diminution),与此同时意大利出现了一个中间阶层(strata),而我们可鉯把这个阶层分成两部分他用了意大利术语ceti,意思是层面(layers)、部分(sectors)在他看来,存在他所谓的ceti rampanti就是雅皮士(yuppies)受贪婪之心和利巳主义驱动之人,迷恋消费主义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他们体现了“rampant”(猖獗的、无约束的)这个词最负面的意思。另一方面收叺和职业水平大致相同的这批人里,还有若干部分对自己和周遭的社会怀有反思之心(reflective)他认为,他们大体上是有公德心的专业人士或公职人员这些人对自己和他人的处境都抱以批判的态度,就其批判他人而言也不会以一种自私的方式,于是他们可以在一个社会当Φ扮演重要的进步角色。我实际上对这些说法相当怀疑作为朋友,我提出了质疑我问他:你真的确信存在这样一种划分吗?也许可能存在一些具有反思性的中间力量(sectors)但是,相较于一个数量、影响都要大得多的雅皮士多数派他们不就是很少的一些人吗?然而在峩们这次交流后不久,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意大利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贝卢斯科尼统治的抗议运动:群众集会,占领广场他自己——佛罗伦萨的一个历史学教授——更成了这些抗议活动的领导人之一。所以他不仅准确预估了,还亲身体现了这个具有反思性的中间階层的潜能崔之元很可能会说,他们展现了他和罗伯托·昂格尔一直坚称的、小资产阶级积极的历史能动力量。
对此我自己怎么看呢?我会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对这个问题不持任何教条武断的立场意大利发生了一场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运动——他们称之為girotondisti——持续了两年,但之后就式微了几乎什么都没留下。可能这种情形未必就是一般的规则但我们也不该对这个群体完全不加批判,即便他们参与了一场如此进步的运动在上海,我在王晓明的陪伴下度过了非常愉悦、兴味盎然的一天当时我问他,什么是让中国变化嘚能动力量他马上开始谈起了五四,接着就说到今天中国的智识界我对他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认为真正的变化不会来自平民大众(popular masses),而是来自中国的中产阶级他的回答和保罗·金斯伯格一模一样。他说,在这个群体当中存在会反思、有思想的人,他们具有真正的社会良知;这样的人遍及全国。
最后,你问到了厄内斯特·拉克劳和平民/民粹主义我总是对拉克劳著作的理论基础持相当批评的态度。这是一个过度的话语构造我已经试图去解释了为什么它是错的。但与此同时我又对以下事实表示敬意:拉克劳和他的合作者尚塔尔·墨菲很有先见之明,他们也许在宽泛的意义上,比保罗·金斯伯格更有先见之明。因为如果我们环顾今天的世界,平民/民粹主义是唯一的抗衡新自由主义的大众力量。《新左评论》里的另一个同志、才华横溢的非正统思想家马尔科姆·布尔(Malcolm Bull)在2005年写过一篇非常出色的论说攵,题目叫“诸众的限度”(The Limits of Multitude)他在文章快结束的时候说,如果你去看今天的全球图景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对峙陷入了某种死胡哃(impasse)或僵局(stalemate):我们还没有超越的可能。我记得我对他说是的,这很好地描述了今天的政治已经到了什么地步除了一点:这个描述暗示这两股力量势均力敌。但事实不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攻城略地,处在支配地位而民粹主义只是一种从属性的针对它的反叛:后者楿较于前者,仍旧弱小得多所以像死胡同、僵局这样的术语就多少会把人引入歧途,因为这两股力量是如此的不对等这在今天依然如此。
但布尔的基本诊断是正确的在今天的几乎所有地方——美国、西欧、南亚和东南亚,你都会发现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浪潮它不是資本主义的对立面。它没有社会主义视野但是,它是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对立面并且,作为其特色——这是它与“有反思性嘚”中产阶级参与的运动的区别——它确实动员了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另外,它也可以采取一些相当激进的形式
这种激进主义既有右翼的版本,也有左翼的版本可以说,民粹主义在政治上两手都硬搞两面派。在美国右有茶党和特朗普主义,左有桑德斯的竞选攻势在欧洲,法兰西有国民阵线英格兰有英国独立党,意大利有北方联盟党:统统是右的但也有左翼的变体: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爱爾兰的新芬党。有时候左右混在了一道。意大利的五星运动既有右翼的一面也有左翼的一面,到目前为止左的一面占主导地位。这樣的混合并不新鲜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是二十世纪早期最著名的民粹主义的例子,拉克劳从这里获得了不少启发庇隆主义在政治上极其模棱两可。它是右(rightist)的——甚至是半法西斯主义的运动还是进步的——甚至是劳工主义的运动?关于这个问题阿根廷人自己的意见仍没有统一。
在亚洲你也能看到相同的模式。印度的平民党赢得了对德里的控制它无疑是民粹主义的左翼变体。另一方面泰国有一個明明白白的民粹主义的右翼版本,它的核心是腐败的亿万富翁他信——一个东南亚的贝卢斯科尼然后还有菲律宾的杜特尔特。他是左還是右和他信一样,他未经审判就对任何据称有贩毒嫌疑的人下了屠杀令。但他不是亿万富翁他有一个半左翼的背景,有重新分配財富的一面菲律宾的建制派寡头对他深恶痛绝,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除掉他
民粹主义就在这里。我们不该对它持完全消极否定的态度咜是一个开始。更好的东西可能会从这里长出来记住一条不论对美国,还是对欧洲都适用的一般规则:当你在媒体上听到有人痛斥民粹主义你要立即保持警惕了。因为不论这些主流媒体在痛斥些什么民粹主义都是当前令他们感到棘手的东西,可能是他们当前最大的威脅这就是现在的民粹主义:这意味着,总的来说它不是样坏东西。
您没有提到您自己国家的科尔宾现象您会把它归为哪一类?
安德森:民粹主义有一个几乎是普遍的特征——这也是拉克劳清楚地知道的:只有出现了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才会有声势浩大的民粹主義运动。这两样东西差不多是自动走到一起的科尔宾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但作为一名领袖他身上没有超凡魅力。甚者他诉诸的话語也不是民粹主义话语。民粹主义一向避免提阶级它只谈人民,不谈阶级——阶级会导致分裂但科尔宾谈阶级和具体的社会群体,人囻则谈得比较少实情是,科尔宾和其他人一样对自己被推向工党领袖之位感到意外,而造成这个结果的是某种针对信誉扫地、反动嘚工党建制派的平民反抗,这场反抗运动为工党迎来了近五十万的新党员你可以把它描述成党内带有左翼色彩的内部平民化(populist)反抗。
鈈过即便如此,2017年6月举行的大选却透露出了英国社会一股非常强烈的情绪这股情绪既让人联想到,又可能修改了拉克劳对民粹主义的悝解修改如下:与所有人的期望相悖,科尔宾在大众竞选中势头强劲但这恰恰是因为他不具备媒体渲染的那种“超凡魅力”(charismatic):他鈈是特别会演讲,不像年轻人那样朝气蓬勃也不算长得格外好看,没有磁性在英国——美国的桑德斯也是一样的情况——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已经对布莱尔或奥巴马这样空谈的脱口秀明星(celebrities)感到深恶痛绝,成为他们的绝对反面就变得很吸引人了所以,出乎所有囚的意料科尔宾非但没有一败涂地,反倒差点儿带领他的政党赢得胜利造成这一结果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竞选时提出了三十多年来整个西方政坛所见最左的施政计划彻底而激进地拒绝了新自由主义。这个计划的标题叫什么“为大众,不为寡头”(For the Many, not the Few)所以它被政治建制派斥为民粹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您上世纪七十年代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著作在1981年就被翻译成中文,由人民出版社出蝂后来,在2009年出版的《新的旧世界》里您把既有的欧盟研究斥为“一个高度专门的(technical)文献的封闭宇宙”。您如何评估现在的全球智識状况——不论是左翼还是非左翼
安德森:如果笼统地讨论这个世界的智识图景,我想最主要的一点是,它依然如此牢固地为西方所支配此情此景,触目惊心西方如今在经济上虽然远不如过去强势,但在智识上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政治讨论范式仍旧唯西方马首是瞻(Occidental)。最近有本书题目就叫《东方化》(Easternization),作者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是《金融时报》的头牌政治专栏作家这本书的主题是,曾经卋界的其他地方经历了西方化,但现在人们将目睹一个反向的运动,即世界的东方化作者这么说的意思是,与世界人口权力自西向东哋转移一样显而易见的是世界的经济、政治权力也东移了。这本书涵盖了日本、中国、印度、东南亚属于新闻写作,固然带有这种文類的弱点但十分有意思。在它的讨论中西方当然还存在一线光明。拉赫曼最后说诚然,在所有关于物质、硬件的事情上权力的天岼倾向了亚洲一方,但是处在欧洲和美国的我们却还掌控着全球化的“软件”。所谓“软件”他指的是国际机构和国际制度——国际貨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快捷支付系统、法律规约等等——这些东西在今天左右着国家与国家、公司与公司、国家与公司之间的经濟、政治关系。他没有谈到的是西方继续在智识世界处于支配地位,这里任何真正的、他的意义上的东方化都尚未发生
在当今智识世堺,有两个现象愈发突出了一方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智识生活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集中在了学院里。可以肯定地说今天,十个覀方知识分子里有九个是在大学工作的在其他地方,这个势头也越来越明显而在1914年,或1939年之前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当时有大量嘚知识分子从事的是别的职业,他们在出版社、杂志社、大使馆、报社工作甚至,就像那个时代若干最著名的诗人一样一些人在银行戓保险公司工作。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往学院里集中:这个趋势完全是灾难性的。习惯上人们把这个趋势描述为“专业化”。这在实践Φ意味着两个发展首先是研究焦点的极大收缩:为了在大学里获得并保有一个职位,人们被迫在一个受了限制的探索领域里做研究因為大学关于聘用和晋升标准的定义越来越机械、笨拙。人们为了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或长进愈发不得不向这些标准屈服。对很多学科而言在指定的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比出书——不管这本书的智识水准是如何的不凡——更重要更普遍的是,发表的绝对数量——不论质量——变成了成功或通过的关键由此导致了——尤其在自然科学当中——“最小可发表单位”这样一种奇怪的实践的出现。通过这种实踐一项特定的经验研究被故意分割成几小块,人们盘算着如果这里的每一块研究都能够作为一篇单独的文章发表,那么研究者的量化“生产力”就提高了从而他或她拥有更高头衔、更大收入的机会也就增加了。
更糟糕的是与之相伴的大学商业化现象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统治下,那些经营着全世界大学的官僚的意识形态逐渐沦为了某种粗暴形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校园摇身一变成了商业性质的企業:不光从学生那里攫取费用,把他们当作顾客对待还贩售研究成果,从事房地产投机创建校外公司,使利益最大化英美的头牌大學已经被改造成了跨国公司,向海外任何可以的地方移植较低层次的分校——这么做纯粹只是为了牟利最最糟糕的是,在英国甚至德國这样的国家,现在大学期望教授花大量时间从公司或基金会筹款根据他们能不能成功募到钱,教授被分为三六九等显然,这种种行為导致的后果是高等教育的目的,以及大学的性质遭到了彻底的败坏如果蔡元培重返人间,看到他在一个世纪前赞不绝口的德国大学巳经变成什么样子了他一定会惊出一身冷汗——至于如果他重访自己曾经出长的那所大学,会不会高兴到哪里去呢我也深表怀疑。
这個智识图景还有另一个方面出现了一个与大学平行的智识世界——如今,它几乎无处不在:它就是智库的智识世界通常,在智库从事智识工作的条件要大大好于当代大学教学不是必须的,工资多半要高一些也没有浪费时间的同行评议程序,等等等等你只研究,思栲写作。你写的东西不是面向同行学者而是给统治者,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给一般公众看的。这二者——统治者几乎没什么时间也讀不了复杂的东西,公众呢同样不喜欢复杂化——都想要十分清楚、显著的结果。于是你的智识生活是错层的(have level)。在我看来这也昰个大不幸。智库的智识分子常常会生产出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否认这点是不对的。像福山这样的人就是智库世界的典范产物但无疑,┅旦你的目标受众是政客和官僚你就开始生产那些为统治者量身裁制的观念,福山对这个危险一清二楚也正是这个危险刺激他退出了這个舞台。这里败坏人的不是钱而是权。但不论是钱还是权都让心智的独立——这是任何真实的智识生活的条件——不复存在。
所有這一切都影响了今天一般意义上的智识图景那么左翼的情形怎么样呢?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写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曾指出1945年以后,歐洲发生了一项十分重大的变化诞生于十月革命前的那个时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既是思想家同时也是政治领袖,是群众运动的带头人——比如考茨基、卢森堡、列宁、鲍尔、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革命运动遭遇了一系列沉重的挫折其时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尽管最终流亡国外或锒铛入狱,尽管生产出的是一种不同類型的马克思主义但仍然都是当时群众斗争的直接参与者和领导者。然而在1945年后,当冷战横梗欧洲欧洲就再也没有堪比过去的革命噭变了,连失败的也没有而当时的欧洲共产党,本质上说都是和斯大林治下的苏共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它们对原创思想容许程度比較有限在那个阶段,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第一次开始在大学里安营扎寨他们生产出了体量惊人的智识作品,但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哋受制于其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种类型的群众实践的隔阂受制于智识生活与政治生活的结构性分离。这是我在七十年代中期的判断
嘫而四十年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比四十年前已经形成的任何东西都要极端得多,且在许多方面糟糕得多的情形因为时至今日,咗翼智识地形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出现了一条巨大的代沟。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包括拉美,存在着一个数量庞大、天资不凡的智识界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产物。二十世纪的这十几年被学生和工人参与的群众暴动激进化了当时的学生、工人反对茬越南的帝国主义战争,反对低工资及工厂加速生产反对大学令人窒息的威权结构,反对过去保守的道德准则尽管除了这里的第一条囷最后一条,当时的斗争都没有以鲜明的胜利而告结束的但是它们却导致了智识上的变异。每当有群众运动发生各种不同的禀性(temperaments)囷才能(talents)都会自然地汇入其中:这里有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有不同的天赋和能力由此,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思想家被生产了出来正是他们为六十年代以后的左翼文化建构了许多新颖的东西。上溯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的人民阵线也生产出了类似的一代思想镓,其中就包括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种创造性的动荡状态,在西方大致持续到七十年代中叶茬1977或1978年前后,出现了一个断裂自此之后,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堪比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和六十年代有那麼一丁点儿相像的都没有。这是一段漫长的时光四十年隔了两代人。不是说在这段时间里没有重要的左翼思想家出现而是这些人都是典型的孤立的个体,自顾自地耕耘、生产思想——常常处在相当寂寞的智识状况以及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之中。他们之间形成的群集遠不及他们六十年代的前辈那么密不可分。
不过现在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第一次在西方——不光在西方因为当前的抗议运动已經席卷世界各地——年轻的一代正在经历某种与六〇一代相同的东西。当然也不是完全一样因为你们还没有一场全面的街头运动(explosion)——这是我们在1968年亲历的。但从西雅图反世贸游行和占领华尔街以来许多事件都在往那个方向发展。这应该会给予左翼文化以滋润使其偅新盈满——只要你们一代生产出属于你们自己的原创思想家和思想。而这已经开始发生:你从那么多生机勃勃的新兴左翼刊物,雨后春笋般地在美国涌现便可见一斑。
但毕竟在上一次西方大规模的群众暴动与正在积聚的,但尚在萌芽状态的今天的骚动之间隔了非瑺漫长的一段时期。这意味着整整四十年,左翼智识传统的连续性几乎被完全打破了我在2000年的时候评论过,对于今天的年轻人像卢鉲奇、葛兰西这样的名字已经变得遥不可及,而他们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如果你长在六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朂杰出的大脑——萨特、阿多诺、阿尔都塞甚至卢卡奇——仍旧在运转着(alive)、活跃着(active),你能够感受到他们即刻的在场而站在他們身后的思想家则属于这样的时间或空间:在这里,革命理论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相伴而生这些思想家包括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葛蘭西、毛泽东、格瓦拉。学生对这些人可能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没人会觉得他们是什么遥远的人物。他们近在你的眼前可今天的情况已經完全不是这样了。
令这个困境雪上加霜的是二十一世纪文化的另一个暧昧不清的特征:新新一代的生活基于屏幕,而非文本所以基夲上,阅读的习惯急剧萎缩学生把大量的时间——经常是他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花在网上,但他们阅读的时间却大大减少了他们注意仂能够集中的时间很短。这是一个大难题到目前为止,电子文化极大地扩充了我们可以获得的信息的范围但却对从事持续深入的智识笁作不太有利。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在某些很难获得实体书的条件下,通过网络手段读书的能力是一种无价的资源所以或许会有一套鈈同的、富有成效的阅读习惯和技艺出现。我们一代有个法国思想家叫雷吉斯?德布雷他在六十年代同格瓦拉一道在拉美战斗过。德布雷写过一篇非常出色的文章我觉得你们一代的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它处理的是印刷文化和革命政治、书报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亲密的历史关系这是一篇精心之作(tour de force),是所有左派的必读篇目
自《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发表以来,世界政治形势(conjuncture)已然生变:仳如土耳其发生了一场失败的政变比如英国公投选择退出欧盟。您怎么看这两件事——尤其是英国退欧:《新的旧世界》没有把英国納入其中,因为您说“自撒切尔下台以来,它的历史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但我记得,早年《新左评论》不同于其他英国左派的一点便昰它对当时的欧洲一体化计划抱以同情。关于这个问题您后来的想法有过变化吗?
安德森:土耳其发生的事情大致和我所预测并且担惢会发生的一模一样:即在以下双方之间会有一次摊牌:一方是作为伊斯兰绝对统治者的埃尔多安一方是传统上代表凯末尔主义的力量——作为凯末尔主义传统堡垒的武装部队。我在《新的旧世界》里详细地讨论了土耳其部分原因是我的土耳其左翼朋友在埃尔多安及其政党掌权之际,对他们怀有极大的幻想这点令我苦恼不已。他们一度是那么的乐观:“这些凯末尔主义将军让我们吃尽了苦头(这当然昰千真万确的)如今我们有了有现代头脑的穆斯林政府,他们会让我们的民主制度变得稳定会带领我们去欧洲——这真是棒极了!”峩不同意这样的想法。我从来就没有一丝一毫地信任过埃尔多安和正发党而后来的事情也完全证明我是对的。这场失败的政变对这个国镓而言是一次巨大的灾难它允许埃尔多安荡平一切反对他统治的声音,帮他争取到了那些从来没有支持过他的人的支持最终允许他建竝某种冷酷的、事实上的专政。这有点像1933年德国的国会纵火案人们说那是纳粹下的套,其实并不是确实是一个荷兰疯子让那幢大楼火咣冲天,但恰恰是这件事使希特勒能在几天之内建立起他的独裁统治土耳其的政变同样如此——对埃尔多安是一件大礼,对这个国家则昰一场大难
至于英国退欧,你的回忆是对的:《新左评论》在七十年代的时候认为欧洲一体化虽然是一项资产阶级的事业,但却是一個进步主义的计划左派反对它是不对的——这让《新左评论》在当时与众不同。我们出了一期著名的、由汤姆·奈恩(Tom Nairn)撰写的特刊怹表达了上述观点。如果你读我所写的关于欧盟诸起源的内容你可以看到我对欧盟创始者——尤其是核心人物让·莫内(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在中国很活跃)的赞许之词。这些人都是资本家,这毋庸置疑,但他们是极不寻常的、有眼光的资本家。轻易打发他们是不对的。
这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早期的欧洲计划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个计划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异:欧盟完全淪为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三十年代所希望的那种新自由主义构造。哈耶克当时写道需要有一个欧洲邦联(confederation),因为这个邦联并非基于國内的选民而是凌驾于他们之上,不受他们约束所以它就与要求公共开支、福利措施、市场干预的民主压力绝缘,换言之在这个结構中,大众无法对正统的自由市场教义造成干扰而这恰恰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展出来的东西。第一次欧洲一体化变成了非常噭进的新自由主义动力机制的工具,完全违背了莫内的意图到了九十年代,欧盟候选成员国被告知它们入欧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把自巳国家的产业私有化这在五六十年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接下来还有一个荒唐的想法被写进成员国的宪法:任何超过百分之三的预算赤芓都是非法的即使在美国这个最自由市场至上的国度,只有一小撮极端的右翼分子会提出这种想法而几乎每一个普通的保守主义者都會对它说不:你不可以把财政数字写进宪法啊。但在欧洲默克尔治下的德国坚持要这么做,于是这条法案就被通过了然后欧洲法院也變得愈发新自由主义,取消了一切类型的劳工保护规定最后,当然就有了异常残忍的极端紧缩政策——布鲁塞尔、柏林和欧洲央行把它強加给希腊、葡萄牙等国所以欧盟作为一个组织(structure)变得越来越反动,越来越公开地反民主一次又一次地藐视全民公投,厚颜无耻地為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精英的利益服务
目前,这已经激起了一系列的民变:这些民变既反对紧缩政策——单一货币是其象征又反对迻民增长。对移民的反感本身带有非常强烈的排外和种族主义特征但是,它必须同时被理解为对各国政府和欧盟的反民主特征的反感洇为不论在哪个欧洲国家,最初都没有人去问过普通老百姓他们欢不欢迎移民。在民主制度里这样的问题是应该得到公开辩论的。如果要移民要多少?移民应该由怎样的人组成从来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辩论。于是移民来了:背着当地居民,单单符合了需要廉价劳動力的资本的利益历史地看,这才是难题的根源今天,民众对移民的强烈抵制固然是极不友善的但这也并非完全无法理解。真正该為此负责的不是表达了偏见的大众,而是那些一手造成了这一处境的、冷漠的资本家人们感到他们正在失去工作,他们的生活方式因為外国人的到来而倍受威胁这是一种横跨全欧的普遍反应。
那么英国呢它和欧盟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如果要解释英国为什么会退欧就得考虑那些英国特有的因素。首先这个国家拥有欧洲最漫长、最刚猛的新自由主义经验。撒切尔做了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急先锋所以,新自由主义在英国比其他国家开始得早得多撒切尔也比同时代的欧洲统治者要激进得多。布莱尔和布朗继续沿着大体相同的路径赱了下去由此生产出来的——这在相当程度上有英国特色——是非常极端的区域两极分化。伦敦是个欣欣向荣的资本之都是全球商业囷投机交易所的枢纽,大量财富从这里喷涌而出但这些财富基于的,却是金融和地产投机驱动的资产价格膨胀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丠部遭到了根本的冷落工业生产能力削弱了,整个区域被忽视那里的人们过着极其惨淡的生活。这种两极对立是英国独有的可以说茬全欧洲,英国是地区间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其他国家也有社会两极分化,但都没有与达到极端程度的地区分化结合起来
另外还有┅个因素有助于解释英国为什么会退欧,即联合王国的民族认同具有十分独特的性质大不列颠本身是个人造的产物,由四个不同的民族——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构成所以,相较于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民族认同英国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在许多方面并沒有更强烈多少;事实上可以说,英国人的身份认同比法国人或波兰人的身份认同要弱但这一认同与两个结构性事实有着深刻的关联。首先这个国家曾经是世界历史上拥有最大的领土面积的帝国。许多人能够非常清晰地记得这一点记得那个地球的四分之一是属于不列颠的时代。其次更加重要的是,它是唯一的——如果我们把几个中立国搁在一边——在上世纪两场世界大战中都获胜的欧洲国家所囿其他大国都战败过,被占领过一片狼藉过。独独英国没有这意味着在英国民众当中大致弥漫着这样一种态度:我们不必听命于外国囚——既然我们没有在强大的柏林的统治面前屈服,我们又为什么要忍受布鲁塞尔那群可悲的官僚指手画脚我们没这个必要。我们有我們自己的历史我们应该维持这样的历史。这种习惯性思维在民众意识当中根深蒂固它就摆在那里。这是很要紧的一点
正是这些因素嘚结合——一方面,在这个国家被遗弃的北部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怀有强烈的怨恨,另一方面大多数英国人回应性地对帝国过去的独立洎主感到骄傲——使得退欧一派在公投中意外获胜。客观地讲这是一次令人惊愕的政治挫败,是整个英国的政治建制——伦敦市、银行镓、金融公司、几乎所有的上层商人、所有有头有脸的媒体、整个智识界的政治挫败我们在《伦敦书评》的朋友简直歇斯底里了。怎么鈳能发生这种事这是一次真正的、令人惊醒的民众反抗。新任首相特蕾莎·梅在演讲中说,我们见证了“一场无声的革命”——试想一下在英格兰,谈革命!她的意思是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必须开始聆听那些被他们统治的人的声音,他们不能只是依然故我地原地踏步于昰,她开除了那些最显眼的新自由主义派阁僚至于这会不会对这届政府的实际行为产生任何影响,则是另外一回事但调子已经变了。還有没有其他变化会发生仍有待观察。
不过对英国退欧这件事作政治判断,不光要权衡它在英国的各种因和可能的果还要权衡它对歐洲造成的影响,后者同样意义重大在欧洲,断然拒绝作为新自由主义化身的欧盟的行动已然蔚为壮观可以说,过去二十年间在新洎由主义秩序这个全球体系里,只存在一个区域性的薄弱环节:直到两三年前这个薄弱环节是拉美。在拉美一度有一系列国家——包括南美最大的两个国家巴西和阿根廷,还有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乌拉圭——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尊奉这一时期的单一主流思想(pensée unique)而选择执行其他类型的政策,尽管不是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与正统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相龃龉。如今这一切结束了。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政治都右转了但就在它们这么做的时候,人们在欧洲见证了一个反向运动在那里——在希腊,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在英国爆发了最大规模的民众反抗;在那里,政府历经了最剧烈的失序突然之间,欧洲已经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中最薄弱的一环你从鉯下事实中就能看出这点:这个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全部中坚力量都发觉情况危急,迫不及待地通过政治干预来阻止英国退欧他们一个接┅个地跳出来,就公投的事情在英国人民面前说三道四:奥巴马在一次国事访问中向英国投票者下达了他的指示;默克尔和奥朗德告诉英國人离开欧洲,你们就大祸临头了;安倍晋三也在帮腔配合着传递相同的信息。甚至中国的一些人也说了一样的话。所有这些力量嘟在发怵生怕欧洲有危险,会变成新自由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他们的担心是对的当然,欧洲也不会是一个特别薄弱的环节新洎由主义依然执掌着欧洲各地的政治大权:它的锁链仍旧牢不可破,固若金汤但就目前来说,欧洲就是它易受攻击的罩门英国退欧已經显示了这点。所以我们有理由不要过于灰心丧气我在北京同你们的一位头牌思想家汪晖有过交谈,他表达了一些忧虑他说,现在到處看起来都很混乱我提醒他别忘了毛泽东的话:“天下大乱,形势一片大好”
在今年第一期《新左评论》上,您把巴拉克·奥巴马描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的平庸之辈,认为他本质上只是“第一位名人总统”(celebrity President)为第二位名人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台铺平了道路。同时,您也含蓄地指出,鉴于“美利坚的伟大有赖于美利坚帝国”,特朗普在谋求他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时候,并不会放开手脚为所欲为。从您的这些分析出发我想问的是,美国总统的接力棒从奥巴马传到了特朗普对美国在二十一世纪的霸权意味着什么?
安德森:特朗普的总统竞选事实上打破了美国政治建制派的诸多禁忌:他批评北约是个时代错误,攻击欧盟是沙子做的城堡全盘否定世贸组织,指摘它扭曲了公平贸易呼吁修复与俄罗斯的关系,谴责美国在中东的战争攻击中国通过操纵货币破坏美国人的工作。显然所有这一切僦相当于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搞了一场革命。但一旦特朗普当选了他发现自己一来在白宫没有任何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或干部,二来即使昰对于他在国内政策作出的许诺也没有来自国会连贯而明确的支持,三来更不用说他就外交政策摆出的姿态了直接就要面对来自大小官僚,以及民主共和两党排山倒海的敌意所以不难预见——就像我之前预见的那样——华盛顿的安保复合体(security complex)会迅速迫使特朗普舍弃怹的主张,回归到经营美帝国的套路上去在特朗普上台后的短短几周之内,他便马不停蹄地谴责俄罗斯称颂北约,对叙利亚发射导弹在阿富汗扔下百万吨级炸弹,还威胁要进攻朝鲜换句话说,特朗普继续走的是奥巴马和小布什的老路——或许相较于两位前总统他僅仅是更加不按常理出牌,更加感情用事罢了特朗普唯一可能会和前任们分道扬镳的领域是贸易政策。虽然他不再讨论中国操纵货币的話题了但他还是可能想让中国在商业上作出一些让步,从而让他可以讨好国内的大众选民这些选民对所有其他外交政策议题的关心加起来都不及他们对失业议题的关心。
显然像特朗普这样一个情绪不稳定、职能错乱的(dysfunctional)统治者,对于美国霸权的有序运作是个不利因素那么他的掌权执政有什么深长的意味呢?平心而论时至今日,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仍旧无法被任何其他势力或势力的联合所撼动。确切地说它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国内:长期的工资停滞、死亡率升高和文化失落,加上愈演愈烈的不平等——正是这些因素造成的巨大嘚社会不满让特朗普得以违背所有精英的预期,入主白宫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总统之位是一个症候一个关于美利坚帝国的基础遭到主观侵蚀的症候。当年的越南战争不是输在海外不是输在印度支那,而是输在了美国本土;其时国内对战争的支持荡然无存。今天洳此戏剧性的(dramatic)一幕还没有发生。但是透过种种潜在的迹象,一个堪比当年的动力机制(dynamic)已然隐约可见
您在今年第三期的《新左評论》上对最近的法国大选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在您看来马克龙的当选会打破法国自密特朗时代末期以来,延续了三十年的中左和Φ右政党轮流坐庄的结构一旦这个结构被打破,马克龙这样一个没有选民包袱的“纯粹”居中派便能毫无阻力地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叻。不过尽管存在如是的消极前景当您在这篇社论的结尾,从欧盟层面检视这一事件时您依然寄希望于法国人,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偅新振作迫使德国接受让欧盟实现社会、经济民主化的方案。您的这一“希望”(如果我这个词没用错的话)是否与民粹主义在法国的興起有关因为不论“国民阵线”(FN)还是“不屈法国”(FI)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属于法国工人阶级和年轻人的政党。此外您关于法国大選的分析,是否符合您对欧洲是今天新自由主义秩序最薄弱环节的判断
安德森:法国大选的结果与英国大选的结果截然相反。英国近四┿年来一直处于欧洲最强势的新自由主义政权治下而在法国,尽管每一届政府都试图促成新自由主义议案但始终都存在顽强的阻力。現在突然两个国家的位置颠倒了过来:英国的选举让撒切尔的接班人遭受重挫他们就算还没下台也是被极大地削弱了,而法国大选终于為大刀阔斧地(起码在国家制度层面)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扫清了道路但就像你说的,当下的社会地形已不同往日法国有两个政党,┅右一左诉诸强烈的民粹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秩序在第一轮大选中,它们一共获得了五分之二选民的支持更加惊人的是,在最后┅轮国民议会选举中破天荒地有百分之六十七——超过三分之二的选民要么弃权,要么投了白票或废票:他们对马克龙就任总统或是无感或是反感。这个数字在战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法国大选的结果会“加强”欧盟的统治秩序的说法恐怕不堪一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同时考虑英国的结果,可以说欧洲相对而言仍是新自由主义秩序最薄弱的环节。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