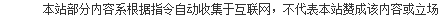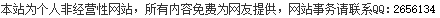受难曰打一肖?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2-05-14 02:35
时间:2022-05-14 02:35
(本文同时发于我们的微信号())
我不博学;我不无知。我懂得欢乐。这说得太少:我活着,而这样的生命给了我最大的快乐。死亡呢?当我死去的时候(或许在此时的任意一刻),我将感到无边的快乐。我说的不是对死亡的预尝,那是索然无味的,通常让人厌恶的。受苦让人迟钝。但这是引人注目的真理,我对此肯定:我在存活中体验到无尽的快乐,我将在死去里得到无尽的满足。
我漂泊过;我从一个地方到过另一个地方。我曾呆在一个地方,住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我曾贫穷,然后更加富裕,然后比许多人更加贫穷。当我是孩子的时候,我拥有巨大的激情,我想要的一切都被给予了我。我的童年已经消失,我的青春在我身后。这不重要。我对曾经存在的感到幸福,我对如今存在的感到满足,即将到来的也合我意。
我的生存比其他人的生存更好吗?或许吧。我有地方住,而许多人没有。我没有麻风病,我没有失明,我看见世界——怎样非凡的幸福!我看见这个白日,在它之外,一无所有。谁能把它从我这儿夺走?当这个白日消逝的时候,我将随它一起消逝:一个思想,一种确然,让我迷狂。
我爱过别人,我失去了他们。当我遭受那样的打击时,我疯了,因为那是地狱。但我的疯狂无人见证,我的精神错乱并不显然;只有我内心深处的存在疯了。有时,我变得暴怒。人们会对我说:“你为何如此镇静?”但我从头到脚被烧焦了;夜间,我会咆哮着跑过街道;白天,我会平静地工作。
不久之后,世界的疯狂爆发了。我被迫像其他许多人一样靠墙站立。为什么?不为什么。枪口没有开火。我对我自己说,上帝,你在做什么?那一刻,我停止了疯狂。世界踟躇着,然后恢复了它的平衡。
随着理性回到我的身上,记忆随之而来,而我看到,甚至是在最坏的日子里,当我认为我是绝对并且彻底悲惨的时候,我也无论如何,几乎一直,是极度幸福的。这给了我些许思考的东西。这一发现并不让人快乐。对我而言,我正失去许多东西。我问我自己,我不悲伤吗,我不是感到我的生命破裂了吗?是的,那是真的;但每一刻,当我起身跑过街道,当我一动不动地待在房间的一隅,黑夜的凉意,大地的稳固,就让我呼吸并倚靠喜悦。
人想要逃离死亡,奇怪的物种。一些人高喊“死,死”因为他们想要逃离生命。“怎样一个生命。我会杀死我自己。我会屈服。”这是可悲的,怪异的;这是一个错误。
但我遇到过一些人,他们从不对生命说“安静!”,从不对死亡说“走开!”几乎总是女人,美丽的造物。人被恐惧所围困,黑夜刺穿了他们,他们看见自己的计划被毁灭,他们看见自己的工作化为尘土。他们曾如此重要,他们曾想创造世界,此时目瞪口呆;一切崩塌了。
我能描述我的厄运吗?我不能行走,或呼吸,或进食。我的气息由石头构成,我的身体由水构成,而我正因干渴而死去。一天,他们把我塞到地里;医生用污泥覆盖了我。在这土地底下,进行着怎样的工作?谁说它是冷的?它是火,是一片荆棘丛。当我起来的时候,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的触觉在我身旁六尺远的地方飘着;如果有人进了我的房间,我会大喊出来,但刀子正把我静静地切断。是的,我成为了一具骷髅。夜晚,我纤瘦的身体会在我面前立起,让我恐惧。它到来又离去,它损害我,它累坏我;哦,我当然很累。
我是一个自我主义者吗?我感到自己只被少数人吸引,不同情任何人,几乎不希望取悦别人,几乎不希望被人取悦,我,在我自己被关心的地方几乎没有感觉,我只在他们中受难,这样,他们的最轻微的不适也成为了一种对我而言无限大的不幸,但即便如此,如果必须,我会慎重地牺牲他们,我会剥夺他们的一切幸福感(有时,我杀了他们)。
我带着成熟的力量从泥坑中出来。我之前是什么?我是一袋子水,一个无生命的延展,一道静止的深渊。(但我知道我是谁;我继续活着,没有坠入虚无。)人们从遥远的地方过来看我。孩子在我身旁嬉戏。女人躺在地上,把她们的手伸给了我。我也年轻过。但空无让我十分失落。
我不胆怯。我到处游荡。有人(一个被激怒了的人)抓住我的手,把他的刀子刺了进去。到处是血。之后,他颤抖着。他把他的手伸给了我,这样,我就可以把它钉在桌子或门上。因为他已经把我那样划开,这个人,一个疯子,虽然他现在是我的朋友;他把他的女人推到我的怀里;他跟着我穿过大街小巷,喊着“我该死,我是一种不道德的精神错乱的玩物,我忏悔,我忏悔。”一个奇怪的疯子。同时,鲜血在我唯一的套装上滴淌。
我绝大多数时候生活在城市里。有一会儿,我过着一种公开的生活。我被法律吸引,我喜欢人群。在他人中间,我默默无闻。我谁也不是,我是至尊。但一天,我厌倦了做一块把孤独者砸死的石头。为了诱惑法律,我温柔地呼唤她,“来这里吧;让我面对面地看着你。”(有一片刻,我想把她带到一旁。)一个鲁莽的恳求。我会做出什么,如果她应答了呢?
我必须承认我读过许多书。当我消失的时候,所有那些书卷会发生难以察觉的变化;边缘会变得更宽,思想会变得更加懦弱。是的,我跟太多的人说过话,到那时为止,我已被打动;对我,每个人都是一整个民族。那庞大的他人,超乎我之意愿地,打造了我。如今,我的生存是令人惊讶地牢固的;就连致死的疾病也认为我过于顽强。请原谅,但我必须在埋葬我自己之前埋掉几个别的人。
我开始陷入贫困。慢慢地,它在我周围画圈;第一道圈似乎给我留下了一切,最后一道圈只给我留下自己。一天,我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城里;旅行不过是一个无稽之谈。我无法打通电话。我的衣服正在破损。我忍受着寒冷;春天,快点吧。我到图书馆去。我和某个工作人员关系密切,他把我带到一个过热的地窖里。为了帮助他,我满心欢喜地沿着狭小的走道飞奔,把书带来,而他随后就把这些书发给阅读的忧郁灵魂。但那个灵魂向我投来并不十分友好的话;我在它眼前缩小;它看到了我是什么,一只虫子,一个从贫困的黑暗王国里钻出的长着双颚的动物。我是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把我抛进了巨大的困惑。
在外面,我得到了一个短暂的景象: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就在我准备离开的街道的拐角上,一个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停下,我不能清楚地看见她,她正操纵着婴儿车好让它通过外门。在那一刻,一个我之前没有看到他过来的男人走进了那扇门。他已经迈过了门槛,但他做了一个停顿并后退的运动。当他待在门边上的时候,从他跟前经过的婴儿车,被稍稍抬了起来,通过了门槛,而年轻的女人,抬头看着他,然后也消失在里面。
这短暂的场景让我兴奋得发狂。我无疑不能向自己完全地解释它,但我可以肯定,我抓住了这样一个瞬间:白日撞上一个真实的事件,开始匆忙地结束。它在这里到来,我对我自己说,终结正在到来;某件事情正在发生,结束就是开始。我陷入了喜悦。
我走向房子但没有进去。通过裂口,我看见了一个庭院的黑色边缘。我斜倚着外墙;我真地很冷。随着寒意从头到脚包裹了我,我慢慢感到我巨大的身高获得了这无尽之寒冷的维度;它,依其真实本性的法则,平静地增长,而我停留在这幸福的喜悦和完美中,有一刻,我的头和天空的石头一样地高,而我的双脚还在碎石路面上。
这一切是真实的;记下来。
我没有敌人。没有人约束我。有时,我脑中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孤独,整个世界在里头消失,但又再次完整地出现,没有一丝的擦伤,没有缺少什么。我几乎失去了我的视力,因为有人把玻璃塞进我的眼睛。那一次打击动摇了我,我必须承认。我感觉我要回到墙里,或流浪到一片燧石丛中。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白日的突然的、恐怖的残酷。我不能看,但我忍不住要看。看让人恐惧,而停止去看把我从前额到喉咙撕开。甚至,我听到了把我暴露给一头野兽之威胁的鬣狗的嚎叫(我想这些嚎叫是我自己发出的)。
玻璃一被取出,他们就在我的眼睑下塞入一块薄膜,又把一层层棉花铺到眼睑上。我不应当说话,因为说话会扯动绷带的棉絮。“你睡着了”,医生后来告诉我。我睡着了!我不得不坚持住,迎战七天的光:一场美妙的大火!是的,一共七天,七天致死的光,成为了一个唯一时刻的火花,责问着我。谁想象过这个?有时,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死亡。不管怎样,它真地值得,它令人难忘。”但通常,我奄奄一息地躺着,并不说话。最终,我开始确信,我直面着白日的疯狂。这就是真相:光发疯了,光明失去了全部的理性:它疯狂地攻击我,失去了控制,没有目的。这一发现径直咬穿了我的生命。
我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不得不听一个人问我,“你要提出控告吗?”对某个刚直接面对着白日的人来说,一个奇怪的问题。
甚至在我痊愈之后,我还怀疑自己是否好了。我不能阅读或写作。我被包围在一片雾气朦胧的北方。但这是奇怪之处:虽然我记得同白日的残酷接触,但我正因在幕帘和墨镜后面生活而日益消瘦。我想要在完全的日光下看到什么;我受够了暗光的快乐和舒适;我对日光有着一种对水和空气一样的欲望。如果看是火,那么,我要求火的丰盈;如果看会让我感染疯狂,那么,我疯狂地想要那样的疯狂。
他们给了我体制内的一个小小的职位。我接电话。医生经营着一个分析实验室(他对血液感兴趣),人们会过来喝某种药。在小床铺上伸开四肢躺着,他们入睡。其中一个人使用了一个非凡的计谋:在喝下正式的产品后,他服毒并陷入昏迷。医生称之为一个龌龊的行为。他把那人弄醒并因这次诈睡“起诉”他。再来一次!在我看来,这个病人应得更好的待遇。
虽然我的视觉几乎完全没有弱化,但我还是像一只螃蟹一样走在街上,紧扶着墙,一旦我松手,眩晕就包围了我的脚步。我常在这些墙上看到同一张海报;它是一张印着大字体的朴实无华的海报:“你也想要这个。”我当然想要,每次我遇到这些显目的词语,我都想要。
但我身上的某种东西很快停止了这个念头。阅读对我而言是一种巨大的疲倦。阅读和说话一样让我精疲力竭,哪怕是我发出的最轻微的真正的言语都要求某种我并不拥有的精力。我得知,“你逆来顺受。”这让我惊讶。二十岁的时候,处于相同的情境,没有人会注意我。到了四十岁,有点贫穷了,我变得凄惨。而这令人不快的表象来自何处?我想我在街上无意间发现了它。街道没有像它们应该的那样让我富有。恰恰相反。当我沿着人行道行走,陷入地铁的明亮灯光,穿过城市宏伟地辐射出来的美丽大道的时候,我变得极度地迟钝,谦卑,疲倦。我收集着无名破烂的多余的部分,接着,我吸引了更多目光的注意,因为这些破烂并不是为我准备的,它们把我变成了某种相当模糊而没有形式的东西;为此,它看起来做作,露骨。贫困的恼人之处在于,它是可见的,任何看见它的人都在想:你瞧,我被指控了;谁在攻击我?但我压根不想把正义带在身上。
他们对我说(有时是医生,有时是护士),“你受过教育,你有才能;如果在十个缺乏能力的人中间分配能力,他们就能活下去,但你保留你的能力,你就剥夺了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而你本可以避免的贫困,则是对其需要的一种冒犯。”我问,“为什么要做这些说教?我在抢我自己的位置吗?把它拿回去吧。”我觉得我被不公的想法和恶意的揣测包围了。他们让我和谁对立?一门不可见的学问,没有人能够证明,我自己则徒然地寻觅。我受过教育!但或许不一直是。有才能?像审判席上穿着长袍,准备夜以继日地谴责我的法官一样说话的那些才能在哪里呢?
我很喜欢医生,我并不觉得自己被他们的怀疑所贬低。烦人的事情在于,他们的权威会按时赫然显现。一个人没有意识到这个,但这些人是国王。他们会突然打开我的房间,并说,“这里的一切归我们了。”他们会攻击我思想的碎屑:“这是我们的。”他们会质问我的故事:“说吧”,而我的故事会服务于他们。匆忙之中,我让自己摆脱了自己。我在他们中间分配我的血液,我内心深处的存在,我把宇宙借给了他们,我把白日给予了他们。就在他们的眼前,虽然他们丝毫没受惊吓,我成为了一滴水,一点墨。我把自己还原为他们。整个的我在他们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消逝;当最终呈现的只有我的完美的虚无,当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他们也不再看到我。他们气急败坏地站起来,大声喊道,“好了,你在哪里?你藏在哪里?躲藏是不允许的,那是违规的”,等等。
在他们身后,我瞥见了法律的身影。不是人人知道的法律,那是严厉的,几乎不讨人喜欢的;这个法律则不同。我根本没有沦为其威吓的牺牲品,我是一个似乎让她恐惧的人。根据她的说法,我的目光是一道闪电,我的双手是毁灭的动机。甚至,法律带着全部的力量荒谬地信任我;她宣称自己永远跪在我的面前。但她没让我做任何的要求,当她认识到我有权在所有地方的时候,那意味着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位置了。当她把我置于权威之上的时候,那意味着“你没有资格做任何事”。如果她低声下气,那意味着,“你不尊重我”。
我知道她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伸张正义”。她会对我说,“现在,你是一个特例;没有人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你言而无罪;誓言不再束缚着你;你可以无所顾忌地行动。你踩在我的身上,我在这里,你永远的奴仆。”奴仆?我无论如何不要一个奴仆。
她会对我说:“你爱正义。”——“是的,我想是的。”——“你为什么让正义在你这个如此非凡的人身上被冒犯?”——“但我个人对我并不非凡。”——“如果正义在你身上变弱,她也会在其他人身上变弱,他们会因此受难。”——“但这不关她的事。”——“一切都关她的事。”——“但如你所说,我是一个特例。”——“只有你行动了,你才是特例——如果你让别人行动,你就绝对不是。”
她说起了无用的话:“真相就是,我们绝不能再次分开。我会四处跟随你。我会在你的屋檐下生活;我们会睡在一起。”
我允许自己被关起来。暂时的,他们告诉我。好的,暂时的。在户外活动期间,另一个住客,一个长着白胡子的老头,跳到我的肩膀上,在我头上比划着。我对他说,“你是谁,托尔斯泰?”为此,医生认为我真地疯了。最终,我背着每个人到处走动,一群紧紧缠着的人,一伙成年人,在那上面被一种统治的徒劳的欲望,一种不幸的童真,怂恿着,当我垮掉的时候(因为我毕竟不是一匹马),我的绝大多数同伴也摔了下来,把我揍了一顿。真是快乐的时光。
法律严厉地批评我的行为:“在我认识你之前,你可不是这样。”——“那是怎样?”——“人们不会拿你取乐而不受惩罚。为了看见你,一个人值得付出生命。爱上你意味着死亡。人们挖坑,并把自己埋在里头,为的是摆脱你的视线。他们会对彼此说,‘他走过去了没有?愿大地隐藏我们。’”——“他们这么怕我吗?”——“畏惧对你来说还不够,发自心底的赞美,一种正直的生活,尘土中的谦卑,也都还不够。首先,不要让人质问我。谁敢想着我?”
她变得奇怪地激动起来。她赞扬我,但只是为了反过来抬高她自己。“你是饥荒,是争执,是谋杀,是毁灭。”——“为什么是这一切?”——“因为我是争执、谋杀与终结的天使。”——“那么”,我对她说,“把我俩关起来都还不够。”真相是我喜欢她。在这个男人过剩的环境里,她是唯一的女性元素。她曾让我触摸她的膝盖:一种奇妙的感觉。我对她说:“我不是那种满足于一只膝盖的人!”她回答:“那真恶心!”
这是她的游戏之一。她会向我展示一部分空间,就在窗户和天花板之间。“你在那里”,她说。我努力看着那个点。“你在那里吗?”我用尽全力看着它。“嗯?”我感觉伤疤飞离了我的双眼,我的视线成了一道伤口,我的头成了一个洞,一头被挖出内脏的公牛。突然,她大喊道,“哦,我看见了白日,哦,上帝”,等等。我抗议这场游戏让我极其疲惫,但她不满足于我的荣耀。
谁把玻璃扔到你脸上?这个问题在其他所有问题中一再出现。它没有被人更加直接地提出,但它是汇聚所有道路的十字路口。他们向我指出,我的回答不会揭示什么,因为一切早已被揭示。“最好不要说。”——“看,你受过教育;你知道沉默引起了注意。你的缄口以更不合理的方式背叛着你。”我会回应他们,“但我的沉默是真实的。如果我对你隐藏了它,你会在稍远的地方重新发现它。如果它背叛了我,那对你反而更好,因为它帮助你,对我也更好,因为你说你正在帮助我。”所以,他们不得不移开天空和大地,直达根底。
我开始加入他们的搜索。我们都像蒙面的猎手。谁被质问?谁在回答?一个人成为了另一个人。词语自言自语。沉默进入了它们,一个完美的避难所,因为我是惟一一个注意到它的人。
我被问到:告诉我们“就在刚才”发生了什么。一个故事?我开始:我不博学;我不无知。我懂得欢乐。这说得太少。我告诉他们整个故事,他们听着,在我看来,还有兴趣,至少是在开始。但结尾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那是开头”,他们说。“现在专心述说事实。”怎么这样?故事结束了!
我不得不承认,我不能从这些事件中形成一个故事。我失去了故事的感觉;那在许多的疾病中发生。但这个解释只是让他们更加苛刻。接着,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们有两个人,并且,传统方法的这一扭曲——即便他们中的一个是眼科医生,另一个是精神病专家的事实解释了这点——把一种受严格法则监督和控制的严厉审问的特点,不断地赋予了我们的谈话。当然,他们俩没有一个是警察局长。但因为有两个,那么他们就有三个人,并且这第三个人始终坚信,我肯定,一个作家,一个在说话和推断上表现出色的人,总能够详细叙述他所记得的事实。
一个故事?不。没有故事,绝不再有。
——————————○●○●○●○●——————————
——————————○●○●○●○●——————————
我要回帖
更多推荐
- ·求一个周线选10倍大牛股周期股价大于ene上轨的选股公式
- ·100种蠢蠢的死法的全民烧脑第41关关怎么过
- ·为什么苹果微信视频镜像是反的咋办的时候镜像反的?
- ·抖音苹果手机安装tiktok为什么不能安装
- ·QQNT的qq可以把聊天记录转移到新手机吗能同步腾讯QQ吗?
- ·倩女手游封号可以换服
- ·他趣怎么玩不容易封号
- ·什么亲手游封号最厉害
- ·失落方舟俄服k区名称
- ·刀剑2修改那些外网IP
- ·侠盗飞车gt5坦克在哪
- ·传奇176圣域勋章爆率
- ·蜀门手游做任务 同一台电脑换5次IP 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吗?
- ·吃鸡国际服几点刷新
- ·多情自古,打一肖?
- ·这是什么游戏?
- ·什么游戏能领包子
- ·嫁娶打一肖
- ·受难曰打一肖?
- ·慢半拍打一数字?
- ·不等式一个小于等于另一个大于有没有公共解?
- ·拼多多怎么查别人有没有用返利?
- ·华藏卫视app大陆用不了
- ·原神账号交易百度知道
- ·微信更到8.0.22,用8.0.0版本违规吗?
- ·百度知道如何提升自己的级别,里边签到有奖为什么不让签到?
- ·我和男朋友说很多消极的话我说被他害了我问他爱不爱我了 他说他想si?
- ·即将收到韵达快递需要报备吗,广东发延庆的?
- ·在澳门能充抖音币吗
- ·做跨境电商该怎么选择代运营公司?
- ·百度知道如何提升自己的级别啊?
- ·在百度知道里,有的问题回答总是显示失败啊,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
- ·把抖音商城:变回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