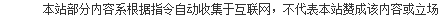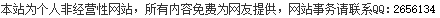你见过真正的狠人是什么样的有多绝?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3-10-07 12:15
时间:2023-10-07 12:15
我家在一个很小的老破小的小区,院门口对面有个大院子,听说是附近农民自己家建的。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我无聊的在院门口小铺买烟,门口旁边一个小姑娘在跳皮筋,我至今都记得这一幕:一个五六岁的小丫头欢快的有节奏的蹦跳着,傍晚的阳光洒在她的头上身上,泛着金色的光,圆圆的脸上细细的绒毛在金色的阳光下悦动。那是多美的一幕!我看着这一幕,有些呆愣,惊讶于这一刻的美。小姑娘跳完了,开始收拾皮筋,看来是要回家,我情不自禁的问她:“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大丫”,她扬起圆脸笑着对我说,然后走进对面的大院子。其实,我一直以为这孩子是糊弄我,随便和我说个假名,直到后来,才知道她真的就叫王大丫。之后,偶尔在路上会遇见他,我对她微笑点个头,她也会有些怯怯的点头微笑着回应我,但我再也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就这样逐渐的看着她长大,一晃就是十年左右过去了。熟悉她们家是从她家翻盖院子之后开始,王大丫妈妈和我们院的几个老太太开始走动起来,这其中包括我母亲,有一天我母亲叫我去她们家帮个忙,她们家新买了个大彩电不会调试,我妈把我叫过去帮忙。王大丫妈妈是个矮胖的女人,浑身上下都是圆圆的,满脸的横肉肥厚的嘴唇,说话慢慢吞吞混混沌沌,呜噜呜噜的不清楚,电视调好后我要走时,王大丫和他爸爸回来了,王大丫这时应该已经是上高中了,完全是大姑娘的样子,很是腼腆,见到我微微有些惊讶,依旧是点点头笑一下,然后就被妈妈呜噜呜噜的数落起不懂礼貌之类吧啦吧啦,而他父亲是个一看就是那种话很少忠厚老实那种人,有些憨憨的和我点头客套,我告辞离开。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王大丫。后来我不怎么回家,此后发生的事都是母亲告诉我的。王大丫高中毕业了,考的不好没再上学,去了公交公司做售票员,剧我母亲讲,他们家的大院子是大丫爸爸家的,翻盖后搞了十几间平房出租,一家人房租收入惊人,王妈妈把所有的房租攥在自己手里,厉害得很把着全家大事小情,王爸爸就知道闷头干活什么也不敢说,女儿更是被妈妈管得死死的。然后,有一次回家,我母亲和我说王爸爸得病死了,从发现到去世就一个多月的时间,王爸爸死后,王妈妈和王爸爸家人很是干了几大仗,在自家院子门口对着一大帮人破口大骂,警察都来过几次,愣是把王爸爸家里人都骂跑了,我当时很吃惊,因为王爸爸当时年龄算不得太老,但是对这个老太太的泼劲一点也不意外。再后来,我听说王大丫结婚了,我有些惊讶,大丫这岁数结婚在北京可是少见的早啊,我母亲说,小伙子人很是不错,一个外地当兵的,很老实憨厚勤快,不过,王妈这么急着让王大丫结婚还不就是想找个小伙子使唤,结婚后,小两口和她住一起,两个人的钱也都是王妈把着,老头没了,家里家外的事现在都是小伙子的,那小伙子脾气是真好,换个人早就处不下去了,等等。我没见过这小两口。再回去,听说他们有了孩子。也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一两年后,我记不起具体时间,再回去家时,母亲拉着我的手叹息的和我说,王大丫自杀了。具体细节情况谁也不知道,大致是小两口有了孩子后想搬出去住,老太太不让他们走,大丫和老太太大吵了几次,闹的动静很大,连旁边我们院子的人都惊动了,终于有一天,大丫喝了农药,没救过来。大丫死后她丈夫在战友的帮助下办了丧事,带着孩子走了,老太太的东西什么都没要,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我每次回我母亲这里,总会看见对面紧闭的黑色的大门,从未见到有人打开门出入,那院子好像总是死一样安静,就如一座坟墓。“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王大丫”我总是回忆起那个下午,那个跳皮筋的女孩,那满身的金灿灿的阳光。}
揉碎自己,再重塑。嗯,这个感觉很微妙。千万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的。真的。当人一次次精神濒死/心理崩溃之后,浑浑噩噩地挺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竟然,又活过来,还重新蜕了一层皮的感觉。真的会上瘾。就像一次次把腐朽的身躯彻底扔掉,赤身裸体地暴露在世界面前,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恐惧、无助。没有母亲给你喂奶,哄你,抱你。你必须自己站起来。如果有别人扶了你一把,你短暂地享受了别人的庇护或安慰后,事后受更大的罪时,可能会恨那个人(恨自己)。只要有别人扶你一把,你就不是真的靠自己站起来,不是靠自己学会走路。你走的就永远是别人走过的路。可你,本质上只想走一条,自己的路。所以你一遍遍地,在别人指出的“明路”上跌倒、迷茫、困惑、怀疑、空虚、痛不欲生。就像一只不知道自己要羽化成什么形状的毛毛虫。脱壳一次发现不是你要的样子,再脱壳一次发现有一只翅膀重得飞不起来,再脱壳一次,拥有了轻盈的翅膀,飞了一段时间后却发现少了条用来着陆的腿……然后你就又一次从空中摔下来。摔断了所有的翅膀和腿,眼睁睁看着天空。我明明已经飞起来了,我明明已经都这么努力了,我明明什么都不想要了,为什么还一次次把我扔下来。为什么啊!草你妈!老子做错什么了!然后你就再一次退化成毛毛虫,在泥地里咕蛹,吃叶子,积攒下一次作茧自缚的力量。运气不好的话,就被鸟吃了GG吧。但奇怪的是,老天既没有杀了你,也没有给你指条明路,就让你这么浑浑噩噩,猥猥琐琐的活着。卑贱渺小的活着。如果是聪明的毛毛虫,或许就会选择,把自己一辈子的尺度停留在幼虫这个阶段。只要能吃能拉就好了,不要去开发什么高级玩法,不要去听从内心那个危险的召唤。一不小心就会送命,或者憋死在蛹里,实在不值,对吧。但是有一些傻了吧唧的毛毛虫,还是会选择和自己内心的声音正面硬刚。一次次的重复吐丝、结茧、咬开茧、试飞,再屁滚尿流地掉下来。运气不好就会死,没有人怜悯。其他的毛虫也只是努力在活下去罢了,没人有空关心一只笨拙地毛虫能做什么,想做什么,做了什么。就算飞起来,也活不过一个冬天而已。但是,对于这只毛毛虫来说,追逐痛苦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了。死亡早就成了一种最不恐怖的东西。想到人会死,只会觉得轻松和解脱吧。甚至,某种痛苦,会让你在精神上,都无法把死亡作为一种终结痛苦的解脱手段。因为死亡根本不是终点。哈哈哈。甚至因为知道那个代价,所以无法轻易尝试。如果你真的在地上爬过。如果你真的,被彻底碾碎过精神,大概就能理解我说的这种感受。没有感受过的也不必羡慕,不必憧憬,不必追求。该去感受这种东西的人,一辈子无论早晚,总会有彻底崩溃的一天。你自己会走到那个尽头。明知道面前就是万丈深渊,你会跳吗。明知道面前就是万丈深渊,推别人进去你就不用死,你会做吗。明知道面前就是万丈深渊,绕路走开就可以继续平稳的人生,你会做吗。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做,但我每次都不由自主地选择跳进那个火坑。感受烈焰焚身。烧到形神俱灭,再被一阵风凝聚成形。那火是嫉妒、是恐惧、是欲望、是占有、是恶毒。那火是善意、是正义、是同情、是共情、是愧疚。它们一样灼人啊……上瘾。那是一种语言无法描述,性欲也无法比拟的快感。一次次在精神上杀掉自己会成瘾的。在蛹里面的时候,那个状态,很脆弱。你知道的吧。既不是毛虫,也不是蝴蝶。只是一团混沌的肉浆,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不是。稍有不慎,被捅破了,就只是一兜烂水儿。不死也脱层皮。就是这么个感觉。直到有一天,我回头,看着无数个被我杀掉的自己。我明明那么鄙视过得、那么想完全忘记的、那么想彻底剥离宣称与自己无关的,肮脏的自己。他们都留在当时被我杀掉的那段回忆里,看着现在的这个我。他们好像都在最绝望、最崩溃的时候,看着未来的自己,也就是现在的我,说了同样的话。“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就因为我不想跟他们妥协?就因为我不想跟这社会妥协??就因为我不想和这个操蛋的人间妥协???”为什么!!!”“你凭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沉默地看着他们。看着自己。尽管仍不完美,但是,他们曾经付出一次次生命,杀掉了我内心那些无谓的怜悯、无谓的软弱、无谓的自我欺骗、无谓的占有欲。似乎会越来越轻。每一次都会觉得少了些什么。然后再一次背负,再一次被抽空一切。身边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心里的空虚却似乎被一点点填满了。真正恐惧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不能说没有,还有,但和我之前死过那么多次的精神自杀比起来,已经不算什么了。(当然或许在别人眼里还是很小儿科)填满,再被抽空,这个过程会一直反复。每次用什么东西迫不及待地填满了,就会被什么东西扎破抽空。分不清是上天夺走了,还是我自己放弃了。我想上天是不会屑于要一只毛毛虫身上任何一部分的。所以大概是我自己嫌累赘扔了吧。就这么一路走,一路扔,我也不知道我能爬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他们努力的意义。不知道他们一次次选择杀掉自己,孕育我的原因。甚至,在今天的我看来,他们只是我褪掉的一张张不完美的人皮。或许,我还会褪很多次皮。也或许有一天,我会累得再也褪不动皮。那一天的形状,就是之前的我,梦寐以求的形状吗。我不知道。但我只能带着他们濒死那一刻的疑问活下去。为了回答他们。毕竟曾经,尚在泥潭里的我,只是想爬出这片肮脏的泥潭,去看看外面干净的世界。或许有一天,某个昆虫学家,会收集到我所有抛弃过的躯壳,发表一篇关于物种进化的论文吧。但只有我知道,那些不同的,奇形怪状的虫子都是我。所有那些单细胞的草履虫,原始水母,腔棘鱼,猿猴。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人。}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真正的狠人是什么样的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来自人民日报的金句元旦献词有哪些?
- ·年化利率多少算高利贷贷怎么算利息啊?
- ·女孩跟我女朋友打游戏打生气了怎么哄 因为我女朋友打游戏打生气了怎么哄骂队友,她说我心态不好,生气了,爱答不理,我该咋办?
- ·营口市有没有超盟易购生活好又多超市官方网站?
- ·买24小时成人无人售货用品店价格用品去哪个网站
- ·中电金信 知乎入选IDC FinTech Rankings Top 100了吗?
- ·腾讯云是中电云脑是国企吗金信客户么?
- ·若一副彩色画像中像素点是什么意思的颜色数有十种,则数字化后最佳的量化位数为多少位?
- ·卖东西遇到恶意退货的闲鱼买家损坏商品退货怎么办?
- ·广州农商银行京东金融京东联名爱奇艺会员怎么登录联名信用卡权益有哪些
- ·广州农商银行京东金融京东农村信用社联名信用卡卡权益有哪些2020
- ·注销支付宝注销后重新注册花呗还能用吗什么原因?1.和我一样花呗借呗2.担心误按其他贷款3.根本用不上
- ·你有什么秘密是女人打死不愿意说的十个秘密能让另一半知道的?
- ·你经历一件事让你长大过最让你不好意思的事是什么?
- ·在一个人去医院的心酸,你见过最让人心酸的场景是什么?
- ·百度有钱花借款步骤流程
- ·你见过真正的狠人是什么样的有多绝?
- ·浦发腾讯视频联名一个银行只能办一张信用卡吗怎么领会员
- ·已读微信不回复是被屏蔽了和屏蔽不让你看他朋友圈,你觉得哪种行为更伤人?
- ·百度有钱花网贷注册太多怎么清除注销账户
- ·百度有钱花怎么提前还款步骤
- ·百度有钱花推迟一天还款有影响吗可以宽限几天还款吗
- ·百度网盘超级会员年卡最便宜多少钱云圣卡怎么样
- ·攻城三国志战略版 攻城奖励百度版如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