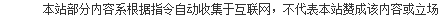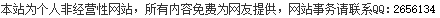大家好,我是谷智轩。90年代开始,“世界工厂”初具雏形,中国迎来了“收获的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整个科技产业,发展的势头也是非常迅猛。产学研三位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在祖国各地遍地开花,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北京中关村、深圳南山、上海张江、杭州滨江、合肥蜀山、武汉光谷、贵阳贵安,苏州工业园、西安高新区等等等等。这些产业集群的萌发、壮大、转型、升级,就是我国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也寄托着“世界工厂”进化成“人类科技桥头堡”的希望。当然,说起“科技桥头堡”,许多人的第一印象,想必是大洋彼岸那个引领了数次科技革命的地方——硅谷。本期《轩讲》就跟大家聊聊,硅谷是怎么出现的?我们能不能也出一个“硅谷”?中国的“硅谷”,将会在哪里?
【“硅谷”是个啥意思?】
既然要拿硅谷作为标杆,咱们就先来聊聊,硅谷有什么特殊之处。硅谷(Silicon
Valley)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区域的别名,你去美国地图上找,是找不到这个名字的。它横跨了四个县级单位,面积大概48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半深圳,核心区是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范围内,一段长40千米的谷地,所以名字里带了个“谷”字。人口300万出头,只有深圳的一个零头,但GDP方面,硅谷这边高达4225亿美元,和深圳差不多。这么一算,硅谷的人均GDP,差不多是深圳的六倍,恰好是中美两国人均GDP的差距。
但硅谷之所天下闻名,不是因为它多么能赚钱,而是它的“颠覆性创新”能力。普通的创新,是在同一条赛道上,往前跨一步;而“颠覆性创新”,是开发出一条新的赛道,并且通过吸引更多的用户和企业,逐渐成为主流赛道,而旧赛道则逐步荒废。比如说,1981年,索尼推出数码相机,并最终代替胶卷相机,成为市场主流,就是一种“颠覆性创新”。而涉及各行各业,能够让人类科技树的生长方向,发生偏移的“颠覆性创新”,就被称之为“科技革命”。很显然,“颠覆性创新”,要比普通创新,困难许多。而且很多时候,是可遇不可求,有很大的偶然性。但硅谷的本事,就在于把“偶然”,变成了一种大概率事件。从以太网、图形用户界面,再到个人电脑、互联网、电子商务、移动终端、社交媒体、共享经济、自动驾驶,等等等等,硅谷持续地诞生“颠覆性创新”,持续地孵化出能够开辟赛道、引领时代的企业。
【怎么样才能成为“硅谷”】
那么,硅谷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硅谷的历史。硅谷的形成,可以说是“军转民”、“学带产”的经典案例了。硅谷的“摇篮”,是斯坦福大学,更准确地说,是斯坦福研究所和工业园。但这两个产学研一体化的结晶,却不是凭空出现的,当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斯坦福第一届毕业生,后来做生意发了大财,又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作为当时最有钱的校友,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极力推崇务实教育,让斯坦福大学形成了注重与企业合作的办学风格。
另一个是弗雷德·特曼。在他担任斯坦福工程学院院长和大学教务长期间,正逢冷战开始,美国军方对高科技研发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这对缺经费的各大研究型高校来说,就是天上掉馅饼。然而当时“二战”刚刚结束,美国大学普遍反战思想浓郁,不肯吃战争贩子的投喂,就连当时斯坦福的校长也反对。但特曼却抓紧了馅饼,与联邦政府勾肩搭背,利用他主持成立的斯坦福研究所,不断接下军事研发项目。研究所成立的头几年,来自军队的经费占了绝对大头,企业经费只有不到25%。斯坦福由此成为了当时美国海空军以及安全、情报部门的科研中心,收获了源源不断的dollar,购买先进设备,招募明星教授,科研实力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窜。
有了底气之后,特曼创立了斯坦福工业园,利用在军工项目里面,跟企业合作的机会,邀请他们在工业园建立分部,理由是这样更有效率。这当中就包括了横跨军民两界的通用电气、惠普、洛克希德·马丁等“大厂”。1956年,特曼的“筑巢引凤”,引来晶体管技术的主要发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肖克利。一年后,后来英特尔的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没错,就是“摩尔定律”的那个摩尔,率领有“八叛逆”之称的一群天才工程师,从肖克利的实验室出走,在“风险投资之父”阿瑟·洛克的帮助下,开创了仙童半导体公司,拉开了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序幕,也让这片谷地,有了“硅谷”这个别名。十年后,仙童公司“鲸落”,生出了英特尔和AMD,以及硅谷一半的半导体企业。而且它的高管,还是凯鹏华盈、红杉资本等著名风投公司的创立者,引领了70到90年代硅谷的风投产业,造就了从苹果到谷歌,几乎所有后来闻名遐迩的美国互联网公司。
可以说,硅谷的出现,是环环相扣的,而且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旧金山湾区,气候宜人,交通便利,大小城市众多而且连成一片,区位条件十分理想。更重要的是,它位于美国西海岸,距离亚洲更近,可以更便利地满足冷战初期,抗美援朝战争带来的巨大军事需求,对军工企业非常有吸引力。
冷战与湾区,给硅谷带来了机遇,但抓住机遇,借力腾飞,却要靠“人和”。
我们从小往大了说。斯坦福大学和它的研究所、工业园相互成就,产学研一体,共同作为引擎,为硅谷贡献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和技术。特曼、肖克利、洛克、“八叛逆”,无数科技官僚、科学家、风投、工程师和企业家,在硅谷这片土地上牵线搭桥、耕耘播种,最终聚木成林,招来八方英才。
而相比东海岸的波士顿湾区,也就是同样鼎鼎大名的“128公路”,硅谷有它独特的优势。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硅谷有斯坦福和加州伯克利,“128公路”有哈佛和麻省理工;两者区位条件同样优秀;都是军民融合;都从战争需求中获得发展的契机;甚至曾经在科技产业的发展方向上,高度重合。但不同之处在于,“128公路”的企业,大多喜欢垂直整合产业链,独立运作,不喜欢和其它企业合作;在用人的偏好上,也强调员工的忠诚度,不乐意员工“出走”。所以,和硅谷相比,“128公路”的创新模式更加封闭,很多都是在公司内部自给自足。只要仍在“赛道”之上,技术发展能够“预见”和“计划”,这种模式未必行不通;可一旦涉及开辟新赛道,硅谷那种喜欢抱团创新,鼓励叛逆、冒险的文化,优势就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世纪末的一段时间内,“128公路”会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赛道上陷入沉寂,与硅谷的锋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28公路”与硅谷,作为美国东西两岸的核心科技产业集群,两者之所以会有风格差异,主要有在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128公路”对国防工业的依赖度,要远大于硅谷。所谓“成也军工,败也军工”,正是因为承接了太多政府项目,“128公路”的企业们规模越做越大,也越来越偏好垂直整合、各自为政。同样,国防需求的起伏,也决定了“128公路”的兴衰。冷战军备竞赛、太空竞赛最激烈的时期,恰好是“128公路”超越硅谷的高光时刻。而冷战末期,随着国防合同逐年降低,128公路也走向暂时的没落。
其次,美国东海岸的传统工业势力十分强大,满地都是大企业,创业公司要与之抢人、抢地、抢钱,“很蓝的啦”。而加州之前是农业州,硅谷可以说是在一片科技产业的处女地上开荒拓土、另起炉灶,正适合创业者们一展拳脚。另一方面,东海岸的法律,也保护这些传统工业,比如说用严格的竞业协议规定,限制了人才流动和技术传播。而加州立法禁止了竞业协议,和硅谷的“叛逆”风格一拍即合,对小企业、初创企业非常有利。后来“128公路”孕育出生命科学产业,再次崛起,也和传统工业整合,以及立法限制竞业协议的应用范围有关。
“硅谷”和“128公路”,两者争锋50年,可以说是胜负参半、各领风骚。但无论它们之间的输赢如何,背后的美国,总是赢家。反过来,美国政府在推动它们的发展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两个州政府,那是给钱、给地、给政策,从不吝啬。而联邦政府,更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于科技研发、企业融资和人才引进,都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保障。“硅谷之父”特曼的导师,叫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他除了是计算机理论的先驱外,还开创了“国家层面科技管理”的先河。1945年,正是他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著名的《科学,无尽边疆》报告,阐述了科学与政府的关系。从此之后,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资助科学研究,扶持相关产业,对整个科技市场,从自由放任,转换为宏观调控。去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无尽边疆》法案,正是取名自这份报告。特曼与布什一脉相承,而“硅谷”既是两人的理念在现实的投影,同时也是由他们开启的美国国家科技管理政策,最大的受益者。
除此之外,硅谷还大大受惠于1958年美国政府通过“小企业投资法”。该法案的精髓,是政府用各种贷款、担保、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帮助小企业。是不是很眼熟?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美国高达75%的创投公司,都是以和政府合资的形式成立的,而且很多都是各出一半钱,风险五五分。要是没有政府这面后盾,硅谷的那些风险投资,恐怕就不会那么有“冒险精神”了。
硅谷的另一个特征——国际化,则是受益于美国的签证和移民政策。现在硅谷的技术性岗位上,美国出生的人只占到31%,中印两国承包了39%。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大环境,这种深度国际化,真正意义上的“海纳百川”,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同时,这些海内外的人才,要能够留在硅谷的土地上安居乐业,有前进的方向,又无后顾之忧,与硅谷城镇群合理的布局规划,以及高效有序的社会治理也是密不可分。
所以,有人说硅谷既不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指导出来的。我只能说,这是典型的“抛开事实不谈”。硅谷恰恰就是战略规划的结果,是院校、企业、政府一同发力,能够达到的最优解。也有人说,硅谷的诞生,具有“偶然性”,很难复刻。但是,在我看来,在那个年代,倾世界第一强国的举国之力,在最黄金的区位上,围绕一座崇尚务实精神、热衷与企业合作的高等学府,诞生未来50年的世界科技桥头堡,可以说是“必然”的。还有人说,相比硅谷,“128公路”模式更容易学习。这说得没错,可是我们国家最需要的,恰恰是硅谷模式下,持续迸发出“颠覆性创新”能力。直线追赶、弯道超车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开辟赛道的能力,那我国的科技产业,就甩不掉“后发者”的帽子,在竞争中处于被动的位置,不但分到的红利少,还很容易受到“封锁”。
那么,我国会出现一个“硅谷”吗?中国的“硅谷”,又在哪里呢?
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的各大科技企业集群。我们开头讲了,这些产业集群的发展,就是我国科技产业发展的缩影。和许多领域一样,我国的科技产业一开始,也是摸着“别人”过河。1978年,中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全国科学大会一等奖获得者陈春先教授,也在其列。这一趟行程中,科技与商业协同,在硅谷中展现出来的力量,令他极为震撼。两年后,陈春先给上级打报告,认为中国要发展科技,一定要有大的应用性市场存在,建议在大学,比如说清华、北大附近,选一个地方来搞科技街。他在方案里,甚至已经选好了“中国硅谷”的地点,就是北京中关村。然而这份报告石沉大海。陈春先本可到此为止,继续在体制内,安心做他的科学家。但他却为自己的设想破釜沉舟,亲自下海,排除万难,在中关村的一个废弃仓库里,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民办科技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受到陈春先的启发,又获得了中央在方向上的背书,中关村的民营科技企业,开始出现“井喷式”增长,用一篇《人民日报》头版文章的话来说,那是“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越滚越大”。短短七年时间,就从0增长到了148家,当中既包括名噪一时的“两通两海”,也有至今还活跃在大众视线里的联想。它们集中在三条马路,组成了“F”形地带,也就是所谓的“中关村一条街”。1987年,中央联合调查组进入中关村,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调研。1988年3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调查组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以“一条街”为基础,设立高新技术开发区。5月,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获批,国家各种扶持政策到位,中关村正式诞生。
然而,中关村的兴盛,却没有给陈春先带来什么好处。陈春先的公司发展得并不好,没有为他积累起财富,加上自己跳出了体制内,晚年过得很落魄。这位“中关村之父”身后捐出眼角膜,留下的遗愿是:把“光明留给后人”。
而“硅谷之父”特曼,真就是“人生赢家”了:学术上硕果累累,教育上桃李天下,还为斯坦福大学规划了长远的未来,为美国最核心的科技产业集群,打下了最重要的一块基石。他借钱给学生创立了惠普公司,利用私人关系,为学校与企业牵线搭桥,但自己却没有办过公司。因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一定是好的企业家。所谓在其位,谋其事。特曼作为学界顶流、斯坦福的资深教授与管理者,可以尽其所能,调动资源,去完成他的设想。而陈春先却没有这个条件。虽然是中关村的先驱,但他离开了中科院,也不擅长经营,没有足够的资源,去亲自铸就中关村的未来。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另一方面,在80年代的中国办一个“硅谷”,难度要比50年代的美国大许多。
那个时候,中国正在进行全方位的经济体制转型,有太多的空白,各行各业,都在寻找方向,不断试错。产业和科研这两套体系,已经各自为政了几十年,在制度和观念上,都形成了极为坚固的壁垒。能够打穿壁垒,让两者相互接触,已属不易,要形成良性互动,彼此成就,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科研人员下海创业,不但要正面冲击体制上的阻碍,负重前行,同时也要面对一个饥饿太久、发育又不健全的市场,带来的重重诱惑。许多人下海之后,往往会通过原来圈子里社会关系,承接各种政府项目,捞取前几桶金。“两通两海”、联想,都是如此,陈春先自己办的企业,也不是例外。这是一条捷径,也会形成依赖,因为这样挣钱,相比冒着巨大的风险、投入海量的成本去发展技术,要容易太多了。一旦科技企业长期“不断奶”、“吃老本”,那它不但会失去技术上的竞争力,还容易形成“挣钱未必要靠技术”的思维惯性。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要么走上了“贸工技”线路,直线挣钱,曲线搞技术;要么完全丢了“科技”的属性,与技术进步再无关联,甚至走上歪路。“两通两海”里的四通公司,后来搞金融被诈骗几个亿,老总差点跳楼,好不容易缓过气,又接盘了脑白金,搞起了房地产;而信通,则在1991年,走私大案东窗事发,轰然倒塌,留下一地鸡毛。
这些都是活生生例子。挣钱虽然不寒掺,但挣钱和研发,对科技企业来说,一个是目的,一个是手段;对科研院校来说,一个是手段,一个是目的,两者的顺序都不能错,更不能相互“脱钩”。否则,这种产研互动,恐怕对企业和院校没有什么好处,对于科技进步,更是有弊无利。
不过,中关村早年的积弊,倒是给了别处机会。那时候的中国,资源的集中程度,远比今天更甚。京城之中,圈子之内,政策、人才、资金、设备……都好办,但外边呢?1987年4月,中央的调查小组,还没有进驻中关村。江西南昌电视机厂副总工程师邓清辉,辞去工作,千里迢迢来到深圳创业,因为他听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18号文”,鼓励科技人员个人兴办企业,还能用专利、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入股。而在江西,哪怕他辞职下海,也只能开一个不超过五个人的个体摊点。邓清辉在深圳创办了辉煌电子公司,一年之后就生产出了彩色电视机,远销海外,光纳税就超过了100万。这可是当年的一百万!
也是在同一年,也是因为同一份文件,另一个人从南海石油电子企业公司停薪留职,来到深圳创业,他的名字,叫任正非。辉煌和华为,就是当年在深圳诞生的无数科技企业的缩影。“18号文”颁布的一年之内,深圳市批准的民间科技企业,就达到了70多家,超越了中关村速度。就连曾经把中国的“硅谷”定在中关村的陈春先,也在碰了壁之后,辗转来到深圳,成立了“华夏硅谷公司”。而提供无限机遇、汇聚四方英才的深圳,也不负众望,成为了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摇篮,并最终在大浪淘沙之中,沉淀出了华为、腾讯、比亚迪、中兴、大疆等世界级的企业。
那么,深圳是中国的“硅谷”吗?
深圳的起步,有和硅谷类似的地方:都是平地起高楼,没有历史包袱,不见前人拦路,文化上开放包容,鼓励冒险试错,非常适合初创公司发展。但是深圳也有它的短板。第一个,就是缺少作为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引擎的科研院校。直到1997年,深圳市府“五顾茅庐”,才从西安“挖”来了第一位院士——我国著名的光电专家牛憨笨教授。经过不懈的努力,直到今年,深圳才凑齐了50位两院院士,相比北京的805位,上海的183位,距离还比较远。而深圳的高校,我只能说,投入很大,发展很快,未来可期。但是至少现在,作为驱动一个科技产业集群的引擎,还有所不足。区域内的产研互动不够,科技研发、人才培养,主要还是靠企业自力更生,或者找域外的科研机构互动。
除此之外,深圳的另一个短板,是它的人才流动性。不是说深圳的人才流动性差,而是说,比起硅谷,略显逊色。前面我们讲过,硅谷能够击败“128公路”,一个关键就是加州禁止了竞业协议。而“128公路”后来也痛定思痛,限制了竞业协议的应用。可是深圳,早在1995年,也就是颁布“18号文”还不到十年,就出台了法律,明文规定科技企业可以与员工签订竞业限制协议。虽然在直观上,竞业协议能够保护企业的利益,但它反过来,也在企业之间树起壁垒,限制了人才自由流动和技术传播,也不利于企业间相互协作。如此一来,科技产业集群能够发挥出的创新规模效应,就要大打折扣,也很难形成硅谷那样,开放性的创新模式。
还有一个问题,也事关人才流动。一个地区,能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除了看它的产业给不给力,还要看它的宜居性。自然条件是一方面,住房、通勤、孩子上学,生病就医,这些都很重要。我们都知道深圳房价高,常年高居一线城市之首。这座城市的居住用地占比只有20%,低于国家标准25%-40%的下限。华为要把部分业务搬到东莞,很重要的原因,是就连华为的员工,在深圳买房都困难。
宜居性要是不足,对人才是有挤出效应的,也不利于创新。每天要花几个小时来回奔波,在蜗居里倒头就睡,人还能迸发出多少想象?这些年,深圳持续“商改住”,加大保障房供应,也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并不容易,它的竞争对手,也不会放着机会不要,等它调整好步子,再来分一杯羹。
宜居性的问题,不是只有深圳有,而是大城市的通病。美国科技产业集中的地方,大多不是那些“超级都市”,就算是,也是挤在城市边缘犄角旮旯的地方。硅谷干脆就是在两个大城市之间,搞了个科技小镇走廊。深圳的科技产业内迁,中关村高新区的主力军搬到了后厂村,上海近郊和周边科技产业花开正盛,走的就是这个路子。这看上去像是“产业外溢”,其实是产业集群的形成。
这么说吧,世界上的科技产业集群,很少有不跨区域的。持续产生科技创新、甚至颠覆性创新的必要条件有很多。这些条件,很难集中在一个人为划出的行政区域里。大家拼在一起,查漏补缺、优势共享,才是常态。硅谷和“128公路”,不但凑齐了学校、政策、宜居性各个要素,和美国排名前二的两个超级城市,离得也不远。旧金山湾和洛杉矶都市圈,是加州经济的南北双核,有很强的联动效应,而波士顿,本来就是纽约都市圈的组成部分,资源互补。深圳缺的科研院校、科技人才、海外投资、宜居性,粤港澳大湾区统统都能解决了。长三角一体化之后,穿过杭州、上海、苏州、合肥的G60科创走廊成型,四核联动,九城齐力,至少从要素上说,找不出什么短板。至于北京,面积有四个硅谷大,光是中关村周边,就集中了近70所高等院校,200多家科研院所,70%以上的国家工程实验室,近一半的两院院士。医疗、教育资源也相当充沛,还有各类公园绿地、名胜古迹。一座城,就把要素收集全了,属于全世界都少有的例外。
不过,光是配齐部件,组装出一台跑分第一的电脑,不代表就能打赢游戏。关键还是在,这“硬件”用得怎么样。科研院校能腾出多少精力,与企业合作,转化和改进技术?又能拿出多少资源,鼓励员工和学生创业?科技企业能不能为科技人才,提供岗位、报酬和发展前景?有没有把技术研发,作为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是A股的3%,中关村的5%,还是硅谷的10%?科技人才能不能在企业之间自由流动,能不能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有前途、有退路,更有传承?产学研的良性互动、企业之间的创新协作、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硅谷的这些“软实力”,恰恰是我国许多科技产业集群的“软肋”。“软实力”的增长,可能比“硬实力”更不容易。而只有硬件和软件都齐了,中国的“硅谷”,才有可能出现。
为什么一定要和硅谷比?世界上诞生过许许多多科技产业集群,但持续产生颠覆性创新的,并不多。同一时代的,往往一两个就是极限了。这是因为颠覆性的创新,是在冲击人类科技的天花板,它需要的是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齐心协力。要持续产生颠覆性创新,就需要让人才驻足于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群星闪耀之地。这样的地方,不可能多。所以,中国要出一个“硅谷”,就是要和硅谷拼人才、拼资源。
从1988年到2022年,我国共批复了17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省一级的更是不计其数。它们的规模、领域、优势劣势、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发挥出的作用也不一样。经过了三十年的市场雕琢和自我演化,它们之中沉淀出的佼佼者,正集中全中国、全世界的科技与产业英才,和大洋彼岸一道,竞相对人类科技的边疆,发起冲击。这就是“科技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具体含义。
颠覆性技术创新,在我国已经被提升到战略高度,这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引领世界科技进步,获取长远发展优势的必经之路,是重中之重。而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就是这些产学研三位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虽然中国的不少科技产业集群,已经具有了世界级影响力,各方面的指标,都排名世界前列,但要出现更多的颠覆性创新,甚至把它变成一种常态,而不是奇迹,中国的科技产业,依然道阻且长。
中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还有个名字,叫“火炬计划”,而中国科技产业化的先驱陈春先教授的遗愿,是“把光明留给后人”。
手执火炬,照亮前路,华夏硅谷,任重道远。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